【2012-09-28】
@whigzhou: #读史笔记#在几十上百年这样的大跨度上,用GDP/收入/消费额之类的指标来衡量发展,除了用作横向比较外,意义似乎不大,恩格尔系数之类能体现消费结构变化的指标更能说明问题,比如可以设计这样一组指标:1)Ci是第i年中等收入消费者的典型消费组合,2)Pi=第i年的Cj价格/第i年中位收入(j=i-10)
@whigzhou: 计算第i年的Cj价格时,条件可放松为:买到的商品组合不必完全一致,功能上不差于它即可,因为10年前的东西可(more...)
【2012-09-28】
@whigzhou: #读史笔记#在几十上百年这样的大跨度上,用GDP/收入/消费额之类的指标来衡量发展,除了用作横向比较外,意义似乎不大,恩格尔系数之类能体现消费结构变化的指标更能说明问题,比如可以设计这样一组指标:1)Ci是第i年中等收入消费者的典型消费组合,2)Pi=第i年的Cj价格/第i年中位收入(j=i-10)
@whigzhou: 计算第i年的Cj价格时,条件可放松为:买到的商品组合不必完全一致,功能上不差于它即可,因为10年前的东西可(more...)
量化宽松既无害也无大用
辉格
2012年9月27日
两周前,美联储推出了总额400亿美元的第三期量化宽松措施(QE3),与规模高达2万亿和6000亿的QE1和QE2相比,这算是超级迷你版了;在一些人看来,联储仍在一意孤行死不悔改的推行其大印钞票的通货膨胀政策,而在另一些(多半也是更接近和了解资本市场的)人看来,与当前经济的萎靡程度相比,这个规模还太小,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在期待不久之后会追加一个QE3.5。
其实这些说法都有些不着边际,那些指责美联储货币政策,多年来每每大呼恶性通货膨胀即将到来的人,无视了(more...)
#第30章#
在第9篇里,我曾说罗氏提出了一个彻底清算财产权的革命纲领,在第11篇里,我们看到这个纲领被扩展了,为第三世界的革命群众提供了指导,号召他们没收外国投资者的资产,然后在第24篇,纲领继续细化,宣布革命群众可以自发动手拿走任何国有资产,在本书最后一章,罗氏最终将革命纲领补充完整了。
曾经听到有些罗粉说,罗氏只是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至于具体怎么实现,他并不负责解答,用罗粉的话说:“别来问我”,听上去好像是个象牙塔里不问世事的哲学家,可是从上面陆续发表的革命纲领看,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再看看罗氏的履历,显然是一位很活跃的政治活动家,而且我们会看到,只想不动可不是他的理念。
罗氏革命纲领大致可分两部分,之前三章里陆续提到的那些,是具体的行动指南,罗氏认为,要取得革命成功,这些行动需要等待恰当的时机,而在时机到来之前,革命者需要做的是意识形态和组织准备,怎么准备法呢?罗氏的回答很干脆:向列宁学习。
所以本章所完成的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列宁式革命纲领,假如你将本章文本中的“自由主义”全部替换成“共产主义”,你可能会误以为那是一份美国共产党的秘密文件,而作者看上去好像接受过共产国际的严格培训。
纲领的首要任务是组织一个列宁式政党,在革命时机成熟之前,该政党将作为自由主义先锋队,向群众宣传灌输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具体做法是,建立一个金字塔形的层次结构,其顶层由少数“核心干部(cadre)”组成,他们对自由主义有着最正确的认识和最坚定的信念,然后下面各层按其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排列。【毫无疑问,罗氏肯定会把自己摆在金字塔的塔尖上,因为从他的论述中不可能得出其他结论】
同时,为了壮大革命事业,该政党将不分左右,与有着某方面共同主张的政治派系建立广泛的战略联盟和统一战线,以便在推进具体政治目标上达成合作。
因为实在不想经历一次类似准备中学政治考试那种噩梦,下面只能少许挑几个段落略作点评,算是领略一下伟大导师的革命风采。
【坐稳了,小心被他的雷倒】
首先,罗氏借阿克顿之口表明了他对渐进主义的坚决拒斥(p.328):
阿克顿这里说的辉格党,显然是指埃德蒙·伯克的辉格党,即辉格党里的保守派,而辉格党里的进步派后来就按阿克顿那条路线发展成了力勃儒,当然不会是他批驳对象。
渐进不行,那么罗氏的激进主义又是如何呢?请看(p.329):
这是废话,假如伯克跟前有这样一键进天堂的按钮,他也会按,换谁都会按,渐进主义者之所以要渐进,并不是因为他们留恋当前状态,想故意拖慢走进天堂的脚步,无非是因为他们相信没有现实可行的更好更快途径,所谓欲速则不达而已。
那么,罗氏是不承认目标与路径存在区分吗?高远纯粹的目标必须对应策略和行动上的激进主义?让我意外的是,他马上否认了这一点(p.329):
咦?这句话好像应该是渐进主义者对罗氏说才对吧?这么说他还是挺现实的?对渐进主义的拒斥只是误解?误以为他们不想快点进天堂?暂时还不清楚,看了例子才知道,不过例子马上来了(p.330):
作为渐进主义或现实主义者,接受一份五年后的废奴方案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不接受的代价可能是:在可见未来都达不成任何废奴方案,如果你的实力不足以控制立法和执法系统,硬来的结果可能就是暴乱和战争,而不硬来的结果就是僵局。
所以我很想有一个例子看看罗氏面临此类困境会怎么处理,还好,接下去的例子比较具体,不过再次提醒你要坐稳了(p.332):
罗氏说,每年减25%预算“没有任何错误”,可是这跟5年后废奴有何不同?因为按罗氏逻辑,答应5年后废奴就意味着同意“4年或更短时间内废奴是错误的”,那么,同意4年内将预算降到零不就等于同意“2年内将预算降到零是错误的”吗?于是“对正义的考虑被抛弃了”吗?
好吧,就按他说的,每年减25%是正确的,可他似乎又暗示原先的提议——每年减10%——是不正确的,否则本来在讨论10%是否正确,还没回答就突然改成25%了呢?可是,既然25%“没有任何错误”,10%怎么就错误了呢?罗氏是怎么算出这么个精确数字的?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雷人的话,接着看(p.332):
意思是,若有10条法律需要废除,必须立即同时废除,若分几次废除,就犯了渐进主义的错误,可是,分3次废除10条法律,和分4次废除预算,究竟有什么不同?设想(more...)
 阿克顿这里说的辉格党,显然是指埃德蒙·伯克的辉格党,即辉格党里的保守派,而辉格党里的进步派后来就按阿克顿那条路线发展成了力勃儒,当然不会是他批驳对象。
渐进不行,那么罗氏的激进主义又是如何呢?请看(p.329):
阿克顿这里说的辉格党,显然是指埃德蒙·伯克的辉格党,即辉格党里的保守派,而辉格党里的进步派后来就按阿克顿那条路线发展成了力勃儒,当然不会是他批驳对象。
渐进不行,那么罗氏的激进主义又是如何呢?请看(p.329):
 这是废话,假如伯克跟前有这样一键进天堂的按钮,他也会按,换谁都会按,渐进主义者之所以要渐进,并不是因为他们留恋当前状态,想故意拖慢走进天堂的脚步,无非是因为他们相信没有现实可行的更好更快途径,所谓欲速则不达而已。
那么,罗氏是不承认目标与路径存在区分吗?高远纯粹的目标必须对应策略和行动上的激进主义?让我意外的是,他马上否认了这一点(p.329):
这是废话,假如伯克跟前有这样一键进天堂的按钮,他也会按,换谁都会按,渐进主义者之所以要渐进,并不是因为他们留恋当前状态,想故意拖慢走进天堂的脚步,无非是因为他们相信没有现实可行的更好更快途径,所谓欲速则不达而已。
那么,罗氏是不承认目标与路径存在区分吗?高远纯粹的目标必须对应策略和行动上的激进主义?让我意外的是,他马上否认了这一点(p.329):
 咦?这句话好像应该是渐进主义者对罗氏说才对吧?这么说他还是挺现实的?对渐进主义的拒斥只是误解?误以为他们不想快点进天堂?暂时还不清楚,看了例子才知道,不过例子马上来了(p.330):
咦?这句话好像应该是渐进主义者对罗氏说才对吧?这么说他还是挺现实的?对渐进主义的拒斥只是误解?误以为他们不想快点进天堂?暂时还不清楚,看了例子才知道,不过例子马上来了(p.330):
 作为渐进主义或现实主义者,接受一份五年后的废奴方案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不接受的代价可能是:在可见未来都达不成任何废奴方案,如果你的实力不足以控制立法和执法系统,硬来的结果可能就是暴乱和战争,而不硬来的结果就是僵局。
所以我很想有一个例子看看罗氏面临此类困境会怎么处理,还好,接下去的例子比较具体,不过再次提醒你要坐稳了(p.332):
作为渐进主义或现实主义者,接受一份五年后的废奴方案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不接受的代价可能是:在可见未来都达不成任何废奴方案,如果你的实力不足以控制立法和执法系统,硬来的结果可能就是暴乱和战争,而不硬来的结果就是僵局。
所以我很想有一个例子看看罗氏面临此类困境会怎么处理,还好,接下去的例子比较具体,不过再次提醒你要坐稳了(p.332):
 罗氏说,每年减25%预算“没有任何错误”,可是这跟5年后废奴有何不同?因为按罗氏逻辑,答应5年后废奴就意味着同意“4年或更短时间内废奴是错误的”,那么,同意4年内将预算降到零不就等于同意“2年内将预算降到零是错误的”吗?于是“对正义的考虑被抛弃了”吗?
好吧,就按他说的,每年减25%是正确的,可他似乎又暗示原先的提议——每年减10%——是不正确的,否则本来在讨论10%是否正确,还没回答就突然改成25%了呢?可是,既然25%“没有任何错误”,10%怎么就错误了呢?罗氏是怎么算出这么个精确数字的?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雷人的话,接着看(p.332):
罗氏说,每年减25%预算“没有任何错误”,可是这跟5年后废奴有何不同?因为按罗氏逻辑,答应5年后废奴就意味着同意“4年或更短时间内废奴是错误的”,那么,同意4年内将预算降到零不就等于同意“2年内将预算降到零是错误的”吗?于是“对正义的考虑被抛弃了”吗?
好吧,就按他说的,每年减25%是正确的,可他似乎又暗示原先的提议——每年减10%——是不正确的,否则本来在讨论10%是否正确,还没回答就突然改成25%了呢?可是,既然25%“没有任何错误”,10%怎么就错误了呢?罗氏是怎么算出这么个精确数字的?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雷人的话,接着看(p.332):
 意思是,若有10条法律需要废除,必须立即同时废除,若分几次废除,就犯了渐进主义的错误,可是,分3次废除10条法律,和分4次废除预算,究竟有什么不同?设想一下,假如你是罗氏的门徒,正在实践他的革命纲领,那么,除了一切行动听他指挥之外,有没有任何办法自行判断自己到底是否正确领会了领袖的意图?
然后,罗氏对他的行动指南做了个小结(p.332):
意思是,若有10条法律需要废除,必须立即同时废除,若分几次废除,就犯了渐进主义的错误,可是,分3次废除10条法律,和分4次废除预算,究竟有什么不同?设想一下,假如你是罗氏的门徒,正在实践他的革命纲领,那么,除了一切行动听他指挥之外,有没有任何办法自行判断自己到底是否正确领会了领袖的意图?
然后,罗氏对他的行动指南做了个小结(p.332):
 意思是,把现状与理想状态相比,凡现状中不应存在于理想状态的那些部分,拿掉一块是一块,这是线性主义制度发展观的清晰表述,关于线性主义,我2007年的一篇文章《理想与路径》和去年的文章《制度变革不是调鸡尾酒》里有详细评论,这里不重复了。
领袖关于列宁式政党或曰先锋队的论述(p.335):
意思是,把现状与理想状态相比,凡现状中不应存在于理想状态的那些部分,拿掉一块是一块,这是线性主义制度发展观的清晰表述,关于线性主义,我2007年的一篇文章《理想与路径》和去年的文章《制度变革不是调鸡尾酒》里有详细评论,这里不重复了。
领袖关于列宁式政党或曰先锋队的论述(p.335):

 关于革命统一战线(p.335):
关于革命统一战线(p.335):
 然后,领袖告诫同志们,要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这两种路线错误(p.336):
然后,领袖告诫同志们,要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这两种路线错误(p.336):
 那么究竟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呢?如果你是美国人,大概想破头想到死也想不明白,不过幸好我学过高中政治课里的唯物辩证法,加上前面刚被雷过一下,很快就领会了:
所谓右倾左倾就是在面临上述现实革命步骤和速度选择时的不同偏向,右倾机会主义的意思是偏向渐进主义,严重的时候就会滑向“投降主义”,成为革命叛徒(比如陈独秀),左倾宗派主义就是偏向激进主义,那为何叫“宗派”呢?因为太激进了就会把不那么激进同志都当成叛徒,而只剩下一小撮自认为革命正宗,于是就宗派主义了(比如王明)。
可是看过前面的雷人部分你就知道,这分寸可实在不好拿捏,在预算那个例子里,分四年废除和立即废除都“没有任何错误”,看来分十年大概是右倾机会主义了,可是左边已经到底了,不知此时左倾是怎么个倾法。
当然,拿捏不准是好事,这样领袖才能保留独断权,想把谁说成某倾主义并打倒在地都很方便,唯如此,才能树立领袖权威嘛。
那么究竟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呢?如果你是美国人,大概想破头想到死也想不明白,不过幸好我学过高中政治课里的唯物辩证法,加上前面刚被雷过一下,很快就领会了:
所谓右倾左倾就是在面临上述现实革命步骤和速度选择时的不同偏向,右倾机会主义的意思是偏向渐进主义,严重的时候就会滑向“投降主义”,成为革命叛徒(比如陈独秀),左倾宗派主义就是偏向激进主义,那为何叫“宗派”呢?因为太激进了就会把不那么激进同志都当成叛徒,而只剩下一小撮自认为革命正宗,于是就宗派主义了(比如王明)。
可是看过前面的雷人部分你就知道,这分寸可实在不好拿捏,在预算那个例子里,分四年废除和立即废除都“没有任何错误”,看来分十年大概是右倾机会主义了,可是左边已经到底了,不知此时左倾是怎么个倾法。
当然,拿捏不准是好事,这样领袖才能保留独断权,想把谁说成某倾主义并打倒在地都很方便,唯如此,才能树立领袖权威嘛。
【2012-09-26】
@仝宗锦 很多人说“何安”,不解,遂度娘之。于是想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段话来:一夫一妻制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人之手——底结果…为了这,就需要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而非男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因为,这种妻方面底一夫一妻制决不妨碍丈夫底公开的或秘密的一夫多妻制。
@whigzhou: 摩根-恩格斯遗毒真是不浅,到现在还时不时有人跟我扯什么“母系社会时代”之类的东东,呵呵
@whigzhou: 谈论配偶制等制度时,人们常使用system而不是institution,这样就无法区分它到底是事实性的还是规范性的,翻译到汉语中,一律变成“某某制”,就更难做此区分了,生物学家谈论的配偶制显然是第一种,制度学家/法学家谈论的显然是后一种,但考察实际制度最多的人类学家常常就晕菜了,往往在两者间跳跃
@whigzh(more...)
有偿沉默怪象根源在发行制度
辉格
2012年9月25日
近日,《新世纪》周刊的一篇报道,将国内资本和新闻市场一个“公开的秘密”推上了舆论的台面,近年来新上市的企业,在IPO过程中,几无例外的会向各大媒体支付一笔“沉默费”,换取后者在该企业IPO审批过程中避免发表负面报道,据说这笔开支已成为发行费用的常规组成,价格也趋于透明,据说每家600万左右,从而“有偿沉默”产业的年规模已达10亿元级。
目前这一局面,据说是媒体与IPO企业双方早些年经历了一番争斗之后所达成的默契,之前更多见的是某些媒体用未发表的负面报道去勒索企(more...)
【2012-09-25】
@瘦驼 请教各位经济学家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的物价是由什么决定的?杭州的物价比烟台便宜真多啊。新白鹿一份一斤的烤鲈鱼才35,一份炒藕片才8块。按说房租,农产品采购成本和人力成本都比烟台高不少。
@whigzhou: 1)许多成本构成项都可以被规模所摊薄,在这方面,消费人群密集的大城市有其优势,2)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之后,许多东西越接近物流集散中心越便宜,3)一种消费品若需求量太小的话,其需求-价格曲线会出现很陡峭的一段,即价格要下降很多才能吸引到新的消费者,此时低价不是好策略
@whigzhou: 关于第3点我曾举过两个例子,第一个很典型,小县城的KTV普遍比大城市价格高,第二个不太典型但更普遍,小县城的小吃/快餐一般比大城市便宜,但点菜的饭馆比大城市贵
@罗伦斯的微博:辉格这么聪明的人,毕竟还是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容易说漏嘴啊。跟兆丰学习去(more...)
#第29章#(续)
【现在总算可以开始检查罗氏对诺齐克的批判了,虽然把前半部分分了出去,篇幅还是有点长】
罗氏一上来便宣称,无论诺齐克是如何论证的,其结论肯定是错的,因为(p.300):
第一条更具体的版本是(p.298):
第一条质疑表明罗氏根本没理解诺齐克在说什么,诺齐克尝试论证的是:从个人无政府主义心目中的理想无政府状态,会自动、合法的滑向有政府状态;他为了让这个讨论得以开始,无条件的接受了你的前提,这是无政府主义能期待的最友善的讨论方式了,罗氏却以为诺齐克是在为现实中的国家辩护,或者是在论证现有国家是如何起源的,实际上人家半个字也没提到现实中的国家。
第二条进一步暴露了罗氏对原文理解存在障碍,诺齐克的论证不正是从“自由市场无政府主义确立之后”这个前提开始的嘛。
第三条着实让人无语,听上去就像:达尔文你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那你就该先把自己变成一只猴子,再静静等待进化过程发挥作用;或者更贴切一点:史密斯你说哪怕是穷人只要勤劳就能致富,那你就该先把自己变成穷光蛋,然后慢慢等着勤劳让你致富。
第四条中的“社会契约论的谬误”具体是指(p.299):
这是罗氏契约理论的老调重弹,确实,按罗氏理论,保护契约很难订立,可是,若适用罗氏契约有效性标准,他口口声声说的保险公司同样无法提供保护服务,比如,为谋杀寻求正义的服务就无法提供,因为罗氏说了(第19章),契约义务不能约束立约人死后的事情,所以一旦你被谋杀,你身前所立契约就全部失效了,保险公司当然就没有义务再帮你寻求正义。
再如,替你追索债务和违约索赔的服务也无法提供,除非你们事先商定服务价格,可是索债和索赔的难度和工作量通常与规模相关,因而通行做法是比例分成,事先无法确定价格,可采用比例分成的契约在罗氏标准下是无效的,因为双方并未交换任何东西,而是约定对某项可能收入进行分成,这样,当实际服务需要出现时,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拒绝提供帮助(或许是因为预感这笔业务太麻烦),因为罗氏说了,除非不履约构成了事实上的偷窃,否则没有义务履约,既然保险公司并未从客户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当然没有履约义务了。
让委托人承诺放弃某些自力救济权,承诺接受某种司法程序的裁决结果的契约条款,更是不可能执行,因为在罗氏看来,这种条款无异于卖身为奴。
问题是,诺齐克的论证前提只是个人无政府主义,而该主义提倡者不止罗氏一人,其他人未必也采用罗氏这种彻底否认承诺效力、毫无契约内涵的契约理论,诺齐克所用的契约,显然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契约。
【打完四棍之后,罗氏总算开始针对诺齐克的具体论证了。】
首先,罗氏拒绝了程序转移条款的必要性(p.300-301):
他轻飘飘的说这“不是不证自明的”,好像诺齐克只是提出而没有论证这一点,这让我怀疑罗氏是否认真阅读了第二章之后的各章,实际上诺齐克花了很多篇幅(包括第三、四两章的预备性论证)来论证程序转移的必要性。
程序转移具有根本重要性,其意义不仅在于让保护组织得以有效履行契约责任,提供质量更高的保护,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制度进化的可能性让无政府主义取得了说服力,假如从无政府状态中无法发展出程序正义,社会仍处于自行裁断、冤冤相报、血仇轮回的状态,那么这种社会根本就是不可欲的。
所以按常理,罗氏本该乐见诺齐克对此条的论证,那为何他会拒斥呢?实际上这反映了罗氏对程序正义的漠视,而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客观主义,客观主义不承认主体间认识差异,因而只需要实质正义,不需要程序正义,在他们看来,事实永远是一清二楚、不存在分歧余地的,“甲侵犯了乙”等同于“乙认为自己受到了甲的侵犯”,这样,乙是选择自力救济,还是诉诸司法程序,在合法性上便没有区别。
接着,罗氏又否定了诺齐克(第6点)对组织间冲突的三种后果的分析(p.301):
他认为保护组织为捍卫其委托人的权利或为其寻求正义而向另一个组织使用暴力,是一种非法的“侵略”行为,可是罗氏明明说过(p.137):“受害者,或受害者的朋友,有权向罪犯施加惩罚吗?答案是当然可以。”
那么为何保护组织就不能算是委托人的朋友呢?难道正式委托关系还不如法律内涵模糊不清的“朋友”关系有效?【说实在,罗氏居然把“朋友”这种概念引入到伦理学中并赋予其如此重要的地位,也算是极品了】假如对方保护组织强行阻止你惩罚罪犯,难道你就只能放弃惩罚了?这么说只要有一个朋友替我出面拦着,我就能随便杀人了?
罗氏又说,对其他组织动用暴力,在经济上也不划算(p.301):
当然,如果只考虑一个案子或一个委托人,那很可能不划算,但由此而建立的“无力帮委托人讨回公道”的声誉却是极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靠收保护费吃饭的黑手党都知道。
不过,罗氏对诺齐克说的第三种可能性(第9点)的分析是正确的(p.301-302):
这我前面已经说过。
接着,罗氏否定了诺齐克(第13、14点)对支配性组织强制其地域内独立个体放弃自力救济权、遵守司法程序的必要性,认为诺齐克的第9点已经解决了这问题(p.304):
其实第9点解决的是组织间分歧,针对的是发生在两个组织的委托人之间的纠纷,而根据第1-4点,能够在保护市场上发展壮大的保护组织,都会采纳程序转移条款,即,他们都已认可程序正义的必要性,只是对何种程序更正义可能存在分歧。
独立个人就不同了,因为他们未与任何保护组织签约,因而其自力救济权不受任何契约约束,所以他的邻居们总是面临着他随时基于自行裁断(很可能是错误的)实施自力救济的危险。
质疑完其必要性之后,罗氏进而质疑其现实合理性(p.305):
独立个人当然可以这么主张,但保护组织的支配地位意味着他没有能力实现这一主张,同样,支配地位的存在也意味着没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不过这倒提醒我们,其实诺齐克(第6点)的组织间对抗还可能产生第5种后果:陷入无休止冲突,而没有任何组织取得支配地位,势力范围也始终稳定不下来,但这只是可能性之一,并不排除其它四种可能性。
第5种可能性实际上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缺陷,诺齐克忽略不提实际上是在照顾无政府主义讨论对手,不知罗氏为何因识破这一点而如此得意。
接着罗氏更进一步,对保护组织以防范危险为由而强制独立个人放弃自力救济权的正当性提出质疑(p.305-306):
然而,诺齐克在第四章里对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已经做出了充分论证,只要你考虑几种现实情形便会发现,这一正当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里我不妨再帮诺齐克补充一下。
比如有人在十米开外举起手枪瞄准你,这显然尚未构成罗氏说的“实际侵犯”,因为到现在为止你还毛发无损,这只是一种危险,甚至他扣下扳机的动作也只是危险而已,你怎么知道枪里一定装着子弹呢?如此说来,即便面对这样的危险,你也不能预防性自卫吗?
不妨将例子再弱化一些,假如你的邻居在紧邻你家卧室的一间仓库里堆满烟花爆竹呢?假如他在你们村子上游拥有一个水库但从不维护其日渐破败的水坝呢?假如他任由自家那几条恶狗在村庄公共道路上肆意乱窜,时而将人咬伤呢?
再举个与自力救济更贴近的例子吧,比如你们隔壁村子住着一群伊斯兰极端分子,公然宣称谁对先知出言不逊,,他们就要灭他全家,甚至他的亲戚朋友邻居也将被视为同伙而受到惩罚,他们不仅如此宣称,还时而(比如每隔几年一次)付诸行动,再比如你们村里住着一个瞒旰狂妄之徒,谁不小心一脚踩进他的稻田就他就把人家的脚砍了。
生活在一(more...)
 第一条更具体的版本是(p.298):
第一条更具体的版本是(p.298):
 第一条质疑表明罗氏根本没理解诺齐克在说什么,诺齐克尝试论证的是:从个人无政府主义心目中的理想无政府状态,会自动、合法的滑向有政府状态;他为了让这个讨论得以开始,无条件的接受了你的前提,这是无政府主义能期待的最友善的讨论方式了,罗氏却以为诺齐克是在为现实中的国家辩护,或者是在论证现有国家是如何起源的,实际上人家半个字也没提到现实中的国家。
第二条进一步暴露了罗氏对原文理解存在障碍,诺齐克的论证不正是从“自由市场无政府主义确立之后”这个前提开始的嘛。
第三条着实让人无语,听上去就像:达尔文你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那你就该先把自己变成一只猴子,再静静等待进化过程发挥作用;或者更贴切一点:史密斯你说哪怕是穷人只要勤劳就能致富,那你就该先把自己变成穷光蛋,然后慢慢等着勤劳让你致富。
第四条中的“社会契约论的谬误”具体是指(p.299):
第一条质疑表明罗氏根本没理解诺齐克在说什么,诺齐克尝试论证的是:从个人无政府主义心目中的理想无政府状态,会自动、合法的滑向有政府状态;他为了让这个讨论得以开始,无条件的接受了你的前提,这是无政府主义能期待的最友善的讨论方式了,罗氏却以为诺齐克是在为现实中的国家辩护,或者是在论证现有国家是如何起源的,实际上人家半个字也没提到现实中的国家。
第二条进一步暴露了罗氏对原文理解存在障碍,诺齐克的论证不正是从“自由市场无政府主义确立之后”这个前提开始的嘛。
第三条着实让人无语,听上去就像:达尔文你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那你就该先把自己变成一只猴子,再静静等待进化过程发挥作用;或者更贴切一点:史密斯你说哪怕是穷人只要勤劳就能致富,那你就该先把自己变成穷光蛋,然后慢慢等着勤劳让你致富。
第四条中的“社会契约论的谬误”具体是指(p.299):
 这是罗氏契约理论的老调重弹,确实,按罗氏理论,保护契约很难订立,可是,若适用罗氏契约有效性标准,他口口声声说的保险公司同样无法提供保护服务,比如,为谋杀寻求正义的服务就无法提供,因为罗氏说了(第19章),契约义务不能约束立约人死后的事情,所以一旦你被谋杀,你身前所立契约就全部失效了,保险公司当然就没有义务再帮你寻求正义。
再如,替你追索债务和违约索赔的服务也无法提供,除非你们事先商定服务价格,可是索债和索赔的难度和工作量通常与规模相关,因而通行做法是比例分成,事先无法确定价格,可采用比例分成的契约在罗氏标准下是无效的,因为双方并未交换任何东西,而是约定对某项可能收入进行分成,这样,当实际服务需要出现时,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拒绝提供帮助(或许是因为预感这笔业务太麻烦),因为罗氏说了,除非不履约构成了事实上的偷窃,否则没有义务履约,既然保险公司并未从客户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当然没有履约义务了。
让委托人承诺放弃某些自力救济权,承诺接受某种司法程序的裁决结果的契约条款,更是不可能执行,因为在罗氏看来,这种条款无异于卖身为奴。
问题是,诺齐克的论证前提只是个人无政府主义,而该主义提倡者不止罗氏一人,其他人未必也采用罗氏这种彻底否认承诺效力、毫无契约内涵的契约理论,诺齐克所用的契约,显然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契约。
【打完四棍之后,罗氏总算开始针对诺齐克的具体论证了。】
首先,罗氏拒绝了程序转移条款的必要性(p.300-301):
这是罗氏契约理论的老调重弹,确实,按罗氏理论,保护契约很难订立,可是,若适用罗氏契约有效性标准,他口口声声说的保险公司同样无法提供保护服务,比如,为谋杀寻求正义的服务就无法提供,因为罗氏说了(第19章),契约义务不能约束立约人死后的事情,所以一旦你被谋杀,你身前所立契约就全部失效了,保险公司当然就没有义务再帮你寻求正义。
再如,替你追索债务和违约索赔的服务也无法提供,除非你们事先商定服务价格,可是索债和索赔的难度和工作量通常与规模相关,因而通行做法是比例分成,事先无法确定价格,可采用比例分成的契约在罗氏标准下是无效的,因为双方并未交换任何东西,而是约定对某项可能收入进行分成,这样,当实际服务需要出现时,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拒绝提供帮助(或许是因为预感这笔业务太麻烦),因为罗氏说了,除非不履约构成了事实上的偷窃,否则没有义务履约,既然保险公司并未从客户那里拿走任何东西,当然没有履约义务了。
让委托人承诺放弃某些自力救济权,承诺接受某种司法程序的裁决结果的契约条款,更是不可能执行,因为在罗氏看来,这种条款无异于卖身为奴。
问题是,诺齐克的论证前提只是个人无政府主义,而该主义提倡者不止罗氏一人,其他人未必也采用罗氏这种彻底否认承诺效力、毫无契约内涵的契约理论,诺齐克所用的契约,显然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契约。
【打完四棍之后,罗氏总算开始针对诺齐克的具体论证了。】
首先,罗氏拒绝了程序转移条款的必要性(p.300-301):
 他轻飘飘的说这“不是不证自明的”,好像诺齐克只是提出而没有论证这一点,这让我怀疑罗氏是否认真阅读了第二章之后的各章,实际上诺齐克花了很多篇幅(包括第三、四两章的预备性论证)来论证程序转移的必要性。
程序转移具有根本重要性,其意义不仅在于让保护组织得以有效履行契约责任,提供质量更高的保护,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制度进化的可能性让无政府主义取得了说服力,假如从无政府状态中无法发展出程序正义,社会仍处于自行裁断、冤冤相报、血仇轮回的状态,那么这种社会根本就是不可欲的。
所以按常理,罗氏本该乐见诺齐克对此条的论证,那为何他会拒斥呢?实际上这反映了罗氏对程序正义的漠视,而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客观主义,客观主义不承认主体间认识差异,因而只需要实质正义,不需要程序正义,在他们看来,事实永远是一清二楚、不存在分歧余地的,“甲侵犯了乙”等同于“乙认为自己受到了甲的侵犯”,这样,乙是选择自力救济,还是诉诸司法程序,在合法性上便没有区别。
接着,罗氏又否定了诺齐克(第6点)对组织间冲突的三种后果的分析(p.301):
他轻飘飘的说这“不是不证自明的”,好像诺齐克只是提出而没有论证这一点,这让我怀疑罗氏是否认真阅读了第二章之后的各章,实际上诺齐克花了很多篇幅(包括第三、四两章的预备性论证)来论证程序转移的必要性。
程序转移具有根本重要性,其意义不仅在于让保护组织得以有效履行契约责任,提供质量更高的保护,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制度进化的可能性让无政府主义取得了说服力,假如从无政府状态中无法发展出程序正义,社会仍处于自行裁断、冤冤相报、血仇轮回的状态,那么这种社会根本就是不可欲的。
所以按常理,罗氏本该乐见诺齐克对此条的论证,那为何他会拒斥呢?实际上这反映了罗氏对程序正义的漠视,而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客观主义,客观主义不承认主体间认识差异,因而只需要实质正义,不需要程序正义,在他们看来,事实永远是一清二楚、不存在分歧余地的,“甲侵犯了乙”等同于“乙认为自己受到了甲的侵犯”,这样,乙是选择自力救济,还是诉诸司法程序,在合法性上便没有区别。
接着,罗氏又否定了诺齐克(第6点)对组织间冲突的三种后果的分析(p.301):
 他认为保护组织为捍卫其委托人的权利或为其寻求正义而向另一个组织使用暴力,是一种非法的“侵略”行为,可是罗氏明明说过(p.137):“受害者,或受害者的朋友,有权向罪犯施加惩罚吗?答案是当然可以。”
那么为何保护组织就不能算是委托人的朋友呢?难道正式委托关系还不如法律内涵模糊不清的“朋友”关系有效?【说实在,罗氏居然把“朋友”这种概念引入到伦理学中并赋予其如此重要的地位,也算是极品了】假如对方保护组织强行阻止你惩罚罪犯,难道你就只能放弃惩罚了?这么说只要有一个朋友替我出面拦着,我就能随便杀人了?
罗氏又说,对其他组织动用暴力,在经济上也不划算(p.301):
他认为保护组织为捍卫其委托人的权利或为其寻求正义而向另一个组织使用暴力,是一种非法的“侵略”行为,可是罗氏明明说过(p.137):“受害者,或受害者的朋友,有权向罪犯施加惩罚吗?答案是当然可以。”
那么为何保护组织就不能算是委托人的朋友呢?难道正式委托关系还不如法律内涵模糊不清的“朋友”关系有效?【说实在,罗氏居然把“朋友”这种概念引入到伦理学中并赋予其如此重要的地位,也算是极品了】假如对方保护组织强行阻止你惩罚罪犯,难道你就只能放弃惩罚了?这么说只要有一个朋友替我出面拦着,我就能随便杀人了?
罗氏又说,对其他组织动用暴力,在经济上也不划算(p.301):
 当然,如果只考虑一个案子或一个委托人,那很可能不划算,但由此而建立的“无力帮委托人讨回公道”的声誉却是极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靠收保护费吃饭的黑手党都知道。
不过,罗氏对诺齐克说的第三种可能性(第9点)的分析是正确的(p.301-302):
当然,如果只考虑一个案子或一个委托人,那很可能不划算,但由此而建立的“无力帮委托人讨回公道”的声誉却是极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靠收保护费吃饭的黑手党都知道。
不过,罗氏对诺齐克说的第三种可能性(第9点)的分析是正确的(p.301-302):
 这我前面已经说过。
接着,罗氏否定了诺齐克(第13、14点)对支配性组织强制其地域内独立个体放弃自力救济权、遵守司法程序的必要性,认为诺齐克的第9点已经解决了这问题(p.304):
这我前面已经说过。
接着,罗氏否定了诺齐克(第13、14点)对支配性组织强制其地域内独立个体放弃自力救济权、遵守司法程序的必要性,认为诺齐克的第9点已经解决了这问题(p.304):
 其实第9点解决的是组织间分歧,针对的是发生在两个组织的委托人之间的纠纷,而根据第1-4点,能够在保护市场上发展壮大的保护组织,都会采纳程序转移条款,即,他们都已认可程序正义的必要性,只是对何种程序更正义可能存在分歧。
独立个人就不同了,因为他们未与任何保护组织签约,因而其自力救济权不受任何契约约束,所以他的邻居们总是面临着他随时基于自行裁断(很可能是错误的)实施自力救济的危险。
质疑完其必要性之后,罗氏进而质疑其现实合理性(p.305):
其实第9点解决的是组织间分歧,针对的是发生在两个组织的委托人之间的纠纷,而根据第1-4点,能够在保护市场上发展壮大的保护组织,都会采纳程序转移条款,即,他们都已认可程序正义的必要性,只是对何种程序更正义可能存在分歧。
独立个人就不同了,因为他们未与任何保护组织签约,因而其自力救济权不受任何契约约束,所以他的邻居们总是面临着他随时基于自行裁断(很可能是错误的)实施自力救济的危险。
质疑完其必要性之后,罗氏进而质疑其现实合理性(p.305):
 独立个人当然可以这么主张,但保护组织的支配地位意味着他没有能力实现这一主张,同样,支配地位的存在也意味着没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不过这倒提醒我们,其实诺齐克(第6点)的组织间对抗还可能产生第5种后果:陷入无休止冲突,而没有任何组织取得支配地位,势力范围也始终稳定不下来,但这只是可能性之一,并不排除其它四种可能性。
第5种可能性实际上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缺陷,诺齐克忽略不提实际上是在照顾无政府主义讨论对手,不知罗氏为何因识破这一点而如此得意。
接着罗氏更进一步,对保护组织以防范危险为由而强制独立个人放弃自力救济权的正当性提出质疑(p.305-306):
独立个人当然可以这么主张,但保护组织的支配地位意味着他没有能力实现这一主张,同样,支配地位的存在也意味着没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不过这倒提醒我们,其实诺齐克(第6点)的组织间对抗还可能产生第5种后果:陷入无休止冲突,而没有任何组织取得支配地位,势力范围也始终稳定不下来,但这只是可能性之一,并不排除其它四种可能性。
第5种可能性实际上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缺陷,诺齐克忽略不提实际上是在照顾无政府主义讨论对手,不知罗氏为何因识破这一点而如此得意。
接着罗氏更进一步,对保护组织以防范危险为由而强制独立个人放弃自力救济权的正当性提出质疑(p.305-306):
 然而,诺齐克在第四章里对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已经做出了充分论证,只要你考虑几种现实情形便会发现,这一正当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里我不妨再帮诺齐克补充一下。
比如有人在十米开外举起手枪瞄准你,这显然尚未构成罗氏说的“实际侵犯”,因为到现在为止你还毛发无损,这只是一种危险,甚至他扣下扳机的动作也只是危险而已,你怎么知道枪里一定装着子弹呢?如此说来,即便面对这样的危险,你也不能预防性自卫吗?
不妨将例子再弱化一些,假如你的邻居在紧邻你家卧室的一间仓库里堆满烟花爆竹呢?假如他在你们村子上游拥有一个水库但从不维护其日渐破败的水坝呢?假如他任由自家那几条恶狗在村庄公共道路上肆意乱窜,时而将人咬伤呢?
再举个与自力救济更贴近的例子吧,比如你们隔壁村子住着一群伊斯兰极端分子,公然宣称谁对先知出言不逊,,他们就要灭他全家,甚至他的亲戚朋友邻居也将被视为同伙而受到惩罚,他们不仅如此宣称,还时而(比如每隔几年一次)付诸行动,再比如你们村里住着一个瞒旰狂妄之徒,谁不小心一脚踩进他的稻田就他就把人家的脚砍了。
生活在一个社区里的未放弃自力救济权的独立个人,就像一个个随机引爆炸弹,不知何时就会以错误认定侵犯为由向他人发起攻击,这些炸弹的存在会让社区邻居随时陷于恐惧之中,而这种恐惧只能通过剥夺其自力救济权、纠正其自力救济习惯,才能消除。
当然,预防性自卫不是没有限度的,判断标准是自卫者对迫近的危险的预期和恐惧是否合理,而这一点无法由先验标准来规定,只能基于经验和直觉感受做判断,而这正是正规司法程序(特别是陪审团)能起作用的地方,若将判断标准交给当事人自行裁断,那么每个人都会认为促使他发起预防性自卫的危险是足够真实而急迫的——这一点反过来又加强了对自力救济习惯进行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
接着,罗氏对诺齐克(第19点)的补偿安排提出了质疑(p.308):
然而,诺齐克在第四章里对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已经做出了充分论证,只要你考虑几种现实情形便会发现,这一正当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里我不妨再帮诺齐克补充一下。
比如有人在十米开外举起手枪瞄准你,这显然尚未构成罗氏说的“实际侵犯”,因为到现在为止你还毛发无损,这只是一种危险,甚至他扣下扳机的动作也只是危险而已,你怎么知道枪里一定装着子弹呢?如此说来,即便面对这样的危险,你也不能预防性自卫吗?
不妨将例子再弱化一些,假如你的邻居在紧邻你家卧室的一间仓库里堆满烟花爆竹呢?假如他在你们村子上游拥有一个水库但从不维护其日渐破败的水坝呢?假如他任由自家那几条恶狗在村庄公共道路上肆意乱窜,时而将人咬伤呢?
再举个与自力救济更贴近的例子吧,比如你们隔壁村子住着一群伊斯兰极端分子,公然宣称谁对先知出言不逊,,他们就要灭他全家,甚至他的亲戚朋友邻居也将被视为同伙而受到惩罚,他们不仅如此宣称,还时而(比如每隔几年一次)付诸行动,再比如你们村里住着一个瞒旰狂妄之徒,谁不小心一脚踩进他的稻田就他就把人家的脚砍了。
生活在一个社区里的未放弃自力救济权的独立个人,就像一个个随机引爆炸弹,不知何时就会以错误认定侵犯为由向他人发起攻击,这些炸弹的存在会让社区邻居随时陷于恐惧之中,而这种恐惧只能通过剥夺其自力救济权、纠正其自力救济习惯,才能消除。
当然,预防性自卫不是没有限度的,判断标准是自卫者对迫近的危险的预期和恐惧是否合理,而这一点无法由先验标准来规定,只能基于经验和直觉感受做判断,而这正是正规司法程序(特别是陪审团)能起作用的地方,若将判断标准交给当事人自行裁断,那么每个人都会认为促使他发起预防性自卫的危险是足够真实而急迫的——这一点反过来又加强了对自力救济习惯进行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
接着,罗氏对诺齐克(第19点)的补偿安排提出了质疑(p.308):
 罗氏认为,补偿不能让对独立个人的权利侵犯正当化和合法化,问题是,按诺齐克的论证,剥夺独立个人的自力救济权本来就是正当合法的预防性自卫,只是不幸的让对方因此而丧失了原本所拥有的权利,所以这里压根不存在合法化问题。
当然,在一个完备自洽的权利划分系统中,本不该出现这样的矛盾:一项正当权利的捍卫需要以剥夺另一项正当权利为代价,可是权利系统未必是完备自洽的,特别是在多中心的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什么原理能担保这一点。
实际上,自力救济权就是最显著的会相互冲突的不自洽权利,当纠纷双方都拥有自认为充足确凿的证据,并因此自行裁定对方侵犯了自己的权利,然后据此实施自力救济,很明显,这种基于自行裁决和对等执行的规范体系内没有任何规则来避免此类冲突。
具体的剥夺自力救济权从而让对方丧失救济手段这一问题,导致系统不自洽的根源,其实是两套救济原则的不一致和不相容,而对这种不相容局面,自力救济这套老原则要负更多责任,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不自洽的,当然就更不可能与其他任何原则构成一个自洽系统。
另一方面,两套救济原则的冲突,也体现人们对“足以让预防性自卫成为正当的真实急迫危险”的判断标准发生了变化,在出现正规司法程序之前,人人都依靠自力救济,因而自力救济权的存在不能被正当的视为支持预防性自卫的“真实急迫危险”,而当正规司法程序出现并普及之后,局面不同了,人们对危险的直觉感受和容忍程度也不同了,因而坚持自力救济权的危险分子已不再是可容忍的了。
当然,对于罗氏这样不承认制度演化的先验主义者,说这些都是白搭,好在我的批判本来就不是写给死人看的。
接着,罗氏又对补偿安排提出更有趣的质疑,认为补偿金额无从计算(p.308):
罗氏认为,补偿不能让对独立个人的权利侵犯正当化和合法化,问题是,按诺齐克的论证,剥夺独立个人的自力救济权本来就是正当合法的预防性自卫,只是不幸的让对方因此而丧失了原本所拥有的权利,所以这里压根不存在合法化问题。
当然,在一个完备自洽的权利划分系统中,本不该出现这样的矛盾:一项正当权利的捍卫需要以剥夺另一项正当权利为代价,可是权利系统未必是完备自洽的,特别是在多中心的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什么原理能担保这一点。
实际上,自力救济权就是最显著的会相互冲突的不自洽权利,当纠纷双方都拥有自认为充足确凿的证据,并因此自行裁定对方侵犯了自己的权利,然后据此实施自力救济,很明显,这种基于自行裁决和对等执行的规范体系内没有任何规则来避免此类冲突。
具体的剥夺自力救济权从而让对方丧失救济手段这一问题,导致系统不自洽的根源,其实是两套救济原则的不一致和不相容,而对这种不相容局面,自力救济这套老原则要负更多责任,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不自洽的,当然就更不可能与其他任何原则构成一个自洽系统。
另一方面,两套救济原则的冲突,也体现人们对“足以让预防性自卫成为正当的真实急迫危险”的判断标准发生了变化,在出现正规司法程序之前,人人都依靠自力救济,因而自力救济权的存在不能被正当的视为支持预防性自卫的“真实急迫危险”,而当正规司法程序出现并普及之后,局面不同了,人们对危险的直觉感受和容忍程度也不同了,因而坚持自力救济权的危险分子已不再是可容忍的了。
当然,对于罗氏这样不承认制度演化的先验主义者,说这些都是白搭,好在我的批判本来就不是写给死人看的。
接着,罗氏又对补偿安排提出更有趣的质疑,认为补偿金额无从计算(p.308):
 罗氏很搞笑的搬出了他在第26章刚刚藐视过的主观价值论,我说过,主观价值论只能在权利边界之内适用,一旦权利边界被突破,或者尚未形成,提出主观价值论除了让事情陷入僵局之外毫无用处,只要坚持主观价值论,任何赔偿问题都无法解决,索赔者完全可以狮子大开口,说被对方摔坏的花瓶比他的生命更重要,所以对方必须偿命。
可是罗氏在第13章不是说要“罪刑均衡”,“绝不能允许一个泡沫胶被偷的商人,对偷窃泡沫胶的小偷处以死刑”吗?可你要是坚持主观价值论,除非被害者认可,你怎么能判断罪刑是否均衡呢?商人为何不能宣称被偷的这块泡沫胶比生命更重要?
要知道,罗氏版本的主观价值论是最最极端的一种,他根本不(像萨缪尔逊那样)承认显示偏好,也不承认偏好稳定性,因而他的主观价值是无法通过之前的交易行为来认定的(p.308):
罗氏很搞笑的搬出了他在第26章刚刚藐视过的主观价值论,我说过,主观价值论只能在权利边界之内适用,一旦权利边界被突破,或者尚未形成,提出主观价值论除了让事情陷入僵局之外毫无用处,只要坚持主观价值论,任何赔偿问题都无法解决,索赔者完全可以狮子大开口,说被对方摔坏的花瓶比他的生命更重要,所以对方必须偿命。
可是罗氏在第13章不是说要“罪刑均衡”,“绝不能允许一个泡沫胶被偷的商人,对偷窃泡沫胶的小偷处以死刑”吗?可你要是坚持主观价值论,除非被害者认可,你怎么能判断罪刑是否均衡呢?商人为何不能宣称被偷的这块泡沫胶比生命更重要?
要知道,罗氏版本的主观价值论是最最极端的一种,他根本不(像萨缪尔逊那样)承认显示偏好,也不承认偏好稳定性,因而他的主观价值是无法通过之前的交易行为来认定的(p.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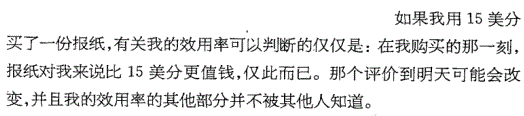 难道罗氏在所有赔偿和救济问题上都要适用主观价值论吗?加上他坚持的自力救济权,我们将会得到怎样一个世界?
下一条质疑更加离奇,罗氏说,诺齐克既然要补偿丧失救济手段的独立个人,那也要补偿那些因其取得支配地位而丧失服务选择机会的人(p.309):
难道罗氏在所有赔偿和救济问题上都要适用主观价值论吗?加上他坚持的自力救济权,我们将会得到怎样一个世界?
下一条质疑更加离奇,罗氏说,诺齐克既然要补偿丧失救济手段的独立个人,那也要补偿那些因其取得支配地位而丧失服务选择机会的人(p.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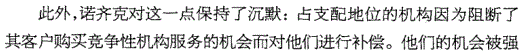 按诺齐克的论证,保护组织的支配地位是经由捍卫自身和委托人权利的过程,以及委托人自愿选择的结果,其垄断是一种自然垄断,按罗氏自由主义,自然垄断显然是正当合法的,为啥要补偿?
再下一条简直是无理取闹了,罗氏说,国家诞生的事实伤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感情,也要补偿(p.309):
按诺齐克的论证,保护组织的支配地位是经由捍卫自身和委托人权利的过程,以及委托人自愿选择的结果,其垄断是一种自然垄断,按罗氏自由主义,自然垄断显然是正当合法的,为啥要补偿?
再下一条简直是无理取闹了,罗氏说,国家诞生的事实伤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感情,也要补偿(p.309):
 我觉得这条再去点评就有点对不起自己了。
接着,罗氏借查尔兹之口质疑补偿安排的负面激励效果(p.310):
我觉得这条再去点评就有点对不起自己了。
接着,罗氏借查尔兹之口质疑补偿安排的负面激励效果(p.310):
 这一质疑第19条里已经预先回答了,不再重复。
接下去罗氏用了不小篇幅对诺齐克在第四章的预备性论证中提出的“非生产性”原则提出了质疑,诺齐克的这条原则我也不大同意,过于功利主义了,不过该原则在他的论证链条上其实并没有用到,更不是必须的,预防性自卫原则足以支持禁止和补偿自力救济权的做法,所以这部分我略过了。
下一条质疑非常重要,我在前面已指出,罗氏伦理学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他根本上否认程序正义,而只承认实质正义,而他对程序正义的否认,根源在于其客观主义,当我发现这一点时,还没看到他明确表述过,现在看到了(p.315-316):
这一质疑第19条里已经预先回答了,不再重复。
接下去罗氏用了不小篇幅对诺齐克在第四章的预备性论证中提出的“非生产性”原则提出了质疑,诺齐克的这条原则我也不大同意,过于功利主义了,不过该原则在他的论证链条上其实并没有用到,更不是必须的,预防性自卫原则足以支持禁止和补偿自力救济权的做法,所以这部分我略过了。
下一条质疑非常重要,我在前面已指出,罗氏伦理学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他根本上否认程序正义,而只承认实质正义,而他对程序正义的否认,根源在于其客观主义,当我发现这一点时,还没看到他明确表述过,现在看到了(p.315-316):
 不过,罗氏否定诺齐克的程序权利的理由却很奇特,本来他应该从他的客观主义哲学除非来否定,不过那么做会显得很荒谬,所以他走了条旁门左道:宣称程序权利是一种类似于积极自由的肯定性权利,而按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对此我举四肢赞成),合格的权利都是否定性的:是规定别人不能对你做什么,而不是你可以做什么。
可是,诺齐克说的程序权利就是否定性的,它规定了别人不能以一种不合格的司法程序来裁定你的是否有罪并据此施以惩罚,假如它是肯定性的,那就意味着别人有义务为你提供一个合格的司法程序,显然,诺齐克并未如此界定程序权利,否则当独立个人与另一个独立个人发生纠纷,就有权要求获得合格司法程序的裁决了,实际上诺齐克并未这么说,相反,正因为独立个人没有这样的肯定性权利,才需要为他与委托人之间的纠纷额外安排一种补偿。
接着,罗氏又借查尔兹之口质疑到:即便诺齐克最弱国家已经诞生,也仍可能退回无政府状态(p.317):
不过,罗氏否定诺齐克的程序权利的理由却很奇特,本来他应该从他的客观主义哲学除非来否定,不过那么做会显得很荒谬,所以他走了条旁门左道:宣称程序权利是一种类似于积极自由的肯定性权利,而按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对此我举四肢赞成),合格的权利都是否定性的:是规定别人不能对你做什么,而不是你可以做什么。
可是,诺齐克说的程序权利就是否定性的,它规定了别人不能以一种不合格的司法程序来裁定你的是否有罪并据此施以惩罚,假如它是肯定性的,那就意味着别人有义务为你提供一个合格的司法程序,显然,诺齐克并未如此界定程序权利,否则当独立个人与另一个独立个人发生纠纷,就有权要求获得合格司法程序的裁决了,实际上诺齐克并未这么说,相反,正因为独立个人没有这样的肯定性权利,才需要为他与委托人之间的纠纷额外安排一种补偿。
接着,罗氏又借查尔兹之口质疑到:即便诺齐克最弱国家已经诞生,也仍可能退回无政府状态(p.317):
 没错,完全可能(见我上篇的第3点评论),但这并不构成一项质疑,因为诺齐克只是论证了国家可能以这种方式诞生,成为最弱国家的支配性组织所获得的支配地位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垄断,而不是排他性垄断权,因而不能保证形成该垄断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诺齐克也并未作此保证。
接着,罗氏又很搞笑的质疑为何诺齐克的这个国家是不征税的(p.318):
没错,完全可能(见我上篇的第3点评论),但这并不构成一项质疑,因为诺齐克只是论证了国家可能以这种方式诞生,成为最弱国家的支配性组织所获得的支配地位只是一种事实上的垄断,而不是排他性垄断权,因而不能保证形成该垄断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诺齐克也并未作此保证。
接着,罗氏又很搞笑的质疑为何诺齐克的这个国家是不征税的(p.318):
 当然,若征税就违反诺齐克设定的道德前提了,不征税不好吗?而且诺齐克也并未将征税设为认定国家存在之标准之一啊,罗氏说:可是现实中的国家都征税啊,可是诺齐克论证的是最弱国家啊,他又没说现实中存在这样的最弱国家嘛;这里,罗氏不知是因为脑筋混乱还是故意捣乱,把保护组织按契约收取的费用说成是税收,又说分不清该向谁收费,可诺齐克明明说了(而且罗氏之前好像一直都清楚),委托人与保护组织的关系是由契约建立的,有契约在还分不清谁是委托人、该向谁收钱?
最后,罗氏又穷极无聊的质疑道:保护组织的保护标准很难确定啊?(p.318):
当然,若征税就违反诺齐克设定的道德前提了,不征税不好吗?而且诺齐克也并未将征税设为认定国家存在之标准之一啊,罗氏说:可是现实中的国家都征税啊,可是诺齐克论证的是最弱国家啊,他又没说现实中存在这样的最弱国家嘛;这里,罗氏不知是因为脑筋混乱还是故意捣乱,把保护组织按契约收取的费用说成是税收,又说分不清该向谁收费,可诺齐克明明说了(而且罗氏之前好像一直都清楚),委托人与保护组织的关系是由契约建立的,有契约在还分不清谁是委托人、该向谁收钱?
最后,罗氏又穷极无聊的质疑道:保护组织的保护标准很难确定啊?(p.318):
 可是罗氏你不是也有提供保护服务的保险公司吗?为啥保险公司的保障标准可以确定,保护组织的保护契约里的保障条款和收费标准就不能确定呢?保护组织不会按市场需求设计保护产品吗?不能随着销售效果和客户反馈而调整产品?这样试错和反馈的过程不能让产品接近客户需求?
说实话,诺齐克的论证远称不上完美,我上篇提出的三点疑问(其实很容易看出)已足够动摇其结论,可是罗氏的表现实在不堪,东拉西扯的质疑没几句站得住脚,在诺齐克这样一位客串玩家面前,可谓颜面丧尽。
可是罗氏你不是也有提供保护服务的保险公司吗?为啥保险公司的保障标准可以确定,保护组织的保护契约里的保障条款和收费标准就不能确定呢?保护组织不会按市场需求设计保护产品吗?不能随着销售效果和客户反馈而调整产品?这样试错和反馈的过程不能让产品接近客户需求?
说实话,诺齐克的论证远称不上完美,我上篇提出的三点疑问(其实很容易看出)已足够动摇其结论,可是罗氏的表现实在不堪,东拉西扯的质疑没几句站得住脚,在诺齐克这样一位客串玩家面前,可谓颜面丧尽。【这篇篇幅实在拖的太长了,我看还是先把前半部分单独分为一篇,这部分是我对诺齐克理论的概述和简评】
#第29章#
本章,罗氏批判了诺奇克(Robert Nozick)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提出的一种国家理论,与第四部分其他各章相比,这一交锋更为正面而直接,因为诺齐克这本书就是对罗氏(和其他人)所主张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回应【许多人以为这本书是针对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其实对《正义论》的回应(构成该书第二部分)只是诺齐克对无政府主义的思考的附带后果】,诺齐克对无政府主义话题的兴趣,最初就来自他1968年与罗斯巴德的一次长谈,在该书第一部分中,这一针对性也非常明确,而且该书后来在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影响极大,所以罗氏当然要花大篇幅重点回应了。
【顺便说一句,诺齐克主要是个分析哲学家,政治和伦理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作为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什么话题都喜欢插个嘴并且较一下真的哲学家,他的业余爱好还有很多,我猜他的课会很好听),这本书在他自己眼里也只是一次兴致盎然的客串而已,客串完之后也没再过多留恋和纠缠。】
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里(另两个部分与这里的话题关系不大),诺齐克试图证明这样一个论点:即便从个人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理想状态出发,经由一系列完全不侵犯个人权利的市场过程,也会产生一个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因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道德指责至少对这样的国家是不成立的(而只适用于超出了这个最低限度的国家)。
为让讨论顺利进行而不在形而上学和经验问题上纠缠,诺齐克在开始论证前,全盘接受了个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前提:一个洛克式的和谐自然状态是可能的,在(more...)
性犯罪不是普通的人身侵犯
辉格
2012年9月21日
本周,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性犯罪和性侵犯的咨询报告,建议对强奸和性侵犯的概念进行一般化,剔除现行法律认定这两类行为时所持的性别和性倾向本位,从而涵盖目前通常以其他罪名起诉的同类行为;法改委是服务于律政司的官方研究咨询机构,其成员在香港司法界具有很高权威,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建议将体现在未来的成文法内,其原则也将在具体案件中被采用。
这是一次对法律规则进行合理化和一般化,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和司法实践的努力,重新界定的强奸和性侵犯罪名所涵盖的新型侵犯行为,此前并非不受惩罚,而是在其他罪名中处理,比如男对男的强行肛交,女对女的器物强行插入,以前可能被当作猥亵或人身伤害或性侵犯而不是强奸,再如性偷窥和裙底偷拍,以前可能作为隐私侵犯处理。
由于现行强奸定义十分狭窄,所以这些行为虽性(more...)
27、28两章内容较简单,而且罗氏所提到的这两位学者(伯林和哈耶克)的观点和言论有许多与我的印象颇有出入,要细究的话需要查对的大量原文,我不打算花这个精力了,所以本篇仅就我与罗氏对这两位思想的认知的重合部分简单说几句,不过好在,我们在主要问题上的印象大致吻合。
#第27章#
罗氏在本章将矛头指向了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理论,在我看来,伯林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辨析区分,为自由主义伦理提供了一块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石,但罗氏否认这一点,可是他的理由比较奇特,主要有两条:1)伯林后来的许多言论偏离了他最初对消极自由的表述,2)伯林有许多与自由主义相抵触的言论。
假如伯林提出两种自由之分是为了建立一套(古典标准的)自由主义伦理,那么你倒是可以说他的努力是失败的,可是伯林显然并无此意,实际上他并不是立场很鲜明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其政治倾向只能算是中间偏右,作为一位分析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他重在概念辨析和思想梳理,而非理论建构。
伯林的一些反市场反资本主义言论,并不让我吃惊,因为他虽然区分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但并未否定积极自由的伦理地位,在他看来,对于一个自由社会,两者都是重要的。
至于罗氏所说的前后表述不一致,我懒得查对,但很可能是他的误解,因为他提到的那些与最初表述不一致的言论中,伯林在说的似乎都是笼统的“自由”,而不是特指“消极自由”,这样的话,与他最初对消极自由的表述不一致也就很正常了,因为他并未拒斥积极自由,所以提到自由时当然可能把后者的涵盖内容也包括进去。
但是,伯林所阐明的消极自由概念确实能够为自由主义伦理提供一块重要的基石,其表述也是足够清晰的(而不是罗氏所暗示的那样,注定是表述不清的),请看伯林1958年在牛津的教席就职演说稿中 标签:
liberty in the negative sense involves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area within which the subject — a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 is or should be left to do or be what he is able to do or be, without interference by other persons'.这个表述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是“area”,可以很自然的转换为我说的行为空间,而引入行为空间的概念可以让我们避免哈耶克所遭遇的困境:如何界定“强制”,因为哈耶克将自由定义为免于强制,可是他始终没能说清楚,到底什么才算强制。【我们马上会看到,这个弱点被罗氏抓住了。】 这样,消极自由的概念其实将自由与(以否定性句式定义的)权利内容上等同了起来,只是词性和语法地位上有所不同:权利是给定边界之内免受打扰的行为空间,而自由是该边界不受侵犯的状态;而在逻辑上,权利先于自由:必须先界定清楚权利,然后我们才能谈论自由;这一等同实际上恢复了古代传统,在大宪章时代,权利与自由原本就近乎于同义词,而且都是从消极意义上界定的。 在权利与自由的关系上,罗氏倒是和我没有分歧,他也认为自由就是权利不受侵犯的状态(p.280):
 区别在于,他的权利是在物理空间上界定的,并且以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比如人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劳动与土壤的结合)为基础,而不是像我那样,在行为空间上界定,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可是,这种界定方式注定解决不了伦理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协调和规范人际关系。
因为许多人可以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行动,这一点无法通过将物理空间的精细划分解决,因为考虑到时序性,无论多小的空间,都可以有多人进入;同样,许多人也可以与同一物品发生关系,仅仅基于人与物的关系而界定权利,实际上回避了人际冲突和拥挤问题,当这些人发生接触和拥挤时,仍没有相应的规范来解决纠纷。
罗氏理论的这一根本缺陷,在第二部分的各篇里已反复暴露过。
#第28章#
本章轮到了哈耶克,前面说了,我同意罗氏在此处对哈耶克的批评,将自由主义伦理仅仅建立在“免于强制”上面,是很难成立的,除非把强制这个概念扩大到非常离谱的程度,而且这种扩大是无原则的,完全是为了满足直觉需要的实用主义式扩展,否则你就无法处理欺诈、背诺、敲诈勒索、剽窃、隐私侵犯等等显然与自由主义相悖的行为范畴。
当然,实用主义也未必不可以,凭直觉罗列一组拇指法则,而不去考究它们的内在逻辑关系,不追求结构井然的统一体系,也未尝不可,但在罗氏这样的先验主义者眼里,这种做法无疑是拙劣的、不可接受的,更满足不了罗氏所设定的“为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可防御的根基”这一要求。
不过按我的方案,这个困难不存在,行为空间上的边界划定之后,只须将“强制”替换为对权利的“侵犯”即可,自由不是免于强制,而是权利免于侵犯,于是问题转换为:权利边界从何而来,而哈耶克的思想恰好为此提供了启示:来自习俗这种自发秩序,也就是合作博弈与协调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信念,在连续迭代过程中,这些信念既来自博弈均衡,也强化和维持着均衡。
罗氏正确的指出了哈耶克的困难【这似乎也是诺齐克所面临的困难,他虽然给出了一些处理方法,但看上去不太理想】,可是他的替代方案却是非常糟糕的,一方面,他沉迷于古老的“物的迷信”中,将人际冲突仅仅理解为物理空间上的冲突,这样,为了确保其消极自由的纯粹性,只好把强制严格限制于“物理上的侵犯”。
这样,他就把欺诈、背诺、敲诈勒索、隐私散布等等显然与自由主义完全不容的行为都合法化了,或者像在商标权和著作权之类的信息财产权问题上,只能用一些无比荒唐的手法来处理(见第17篇),可以说,他察觉到了困难,但没有认真严肃的去处理,而是像面对难题无计可施的宠坏小孩那样采取了躺倒策略,往地上一躺,四腿一伸,宣布我啥也不搭理了。
区别在于,他的权利是在物理空间上界定的,并且以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比如人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劳动与土壤的结合)为基础,而不是像我那样,在行为空间上界定,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可是,这种界定方式注定解决不了伦理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协调和规范人际关系。
因为许多人可以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行动,这一点无法通过将物理空间的精细划分解决,因为考虑到时序性,无论多小的空间,都可以有多人进入;同样,许多人也可以与同一物品发生关系,仅仅基于人与物的关系而界定权利,实际上回避了人际冲突和拥挤问题,当这些人发生接触和拥挤时,仍没有相应的规范来解决纠纷。
罗氏理论的这一根本缺陷,在第二部分的各篇里已反复暴露过。
#第28章#
本章轮到了哈耶克,前面说了,我同意罗氏在此处对哈耶克的批评,将自由主义伦理仅仅建立在“免于强制”上面,是很难成立的,除非把强制这个概念扩大到非常离谱的程度,而且这种扩大是无原则的,完全是为了满足直觉需要的实用主义式扩展,否则你就无法处理欺诈、背诺、敲诈勒索、剽窃、隐私侵犯等等显然与自由主义相悖的行为范畴。
当然,实用主义也未必不可以,凭直觉罗列一组拇指法则,而不去考究它们的内在逻辑关系,不追求结构井然的统一体系,也未尝不可,但在罗氏这样的先验主义者眼里,这种做法无疑是拙劣的、不可接受的,更满足不了罗氏所设定的“为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可防御的根基”这一要求。
不过按我的方案,这个困难不存在,行为空间上的边界划定之后,只须将“强制”替换为对权利的“侵犯”即可,自由不是免于强制,而是权利免于侵犯,于是问题转换为:权利边界从何而来,而哈耶克的思想恰好为此提供了启示:来自习俗这种自发秩序,也就是合作博弈与协调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信念,在连续迭代过程中,这些信念既来自博弈均衡,也强化和维持着均衡。
罗氏正确的指出了哈耶克的困难【这似乎也是诺齐克所面临的困难,他虽然给出了一些处理方法,但看上去不太理想】,可是他的替代方案却是非常糟糕的,一方面,他沉迷于古老的“物的迷信”中,将人际冲突仅仅理解为物理空间上的冲突,这样,为了确保其消极自由的纯粹性,只好把强制严格限制于“物理上的侵犯”。
这样,他就把欺诈、背诺、敲诈勒索、隐私散布等等显然与自由主义完全不容的行为都合法化了,或者像在商标权和著作权之类的信息财产权问题上,只能用一些无比荒唐的手法来处理(见第17篇),可以说,他察觉到了困难,但没有认真严肃的去处理,而是像面对难题无计可施的宠坏小孩那样采取了躺倒策略,往地上一躺,四腿一伸,宣布我啥也不搭理了。
【2012-09-20】
@恶人谷江小鱼: 我发起了一个投票 【特大钻石矿如被证实,黄金价格将:】,期待着你的参与,快来参加吧! http://t.cn/zlZJAAH
@sw小橘子 我投给了”涨” 这个选项
@whigzhou: 这事未必有多大影响,光蕴藏量大没用,要看这矿的开采速度和成本曲线,除非速度极快、成本极低且不随产量上升,否则不会有颠覆性影响
@sw小橘子: 事关人们对钻石稀缺性的信心吧
@whigzhou: 你是说钻石的投资品功能?我看不出钻石有多少这种功能,这东西又不像黄金,价值分歧大、切割麻烦、转手不容易,好像没什(more...)
留学热潮遭遇供给瓶颈
辉格
2012年9月19日
最近,社科院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留学生最大来源国,2011年共输出了34万留学生,占全球总数的14%,这34万学生大约一半是去美国留学,从而在美国市场上也以22%的比例取代印度学生而成为最大留学族群;这一状况,是过去12年以28%的年率迅猛增长的结果,如今每年的留学人数已1.5倍于2000年之前22年的总和。
这股留学热潮是全球性的,全球留学生的年增长率尽管远低于中国水平,也高达12%,而且目前还看不出这股热潮会消退的任何迹象;推动这股热潮的一大动力,(more...)
【罗粉已经好久没动静了,让我的批罗工作也变得兴味索然起来,哎~】
在之前第三部分的四章里,罗氏集中阐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理论,但其实他只是说了一大堆国家之恶,并未给出一个实际的(无论是否可行也无论好不好)无政府主义替代方案,在即将进入的第四部分,罗氏将对支持自由市场的其他几种备选理论作了评论,并一一加以否决,结论是:只有他的伦理学能支持得住自由市场。
#第26章#
罗氏在本章批判了功利主义哲学,认为它不可能为自由市场提供理论基础(p.263):
不过罗氏的批判矛头指向很不明确,把功利主义的各种可能版本混杂在一起批,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不区分其中的伦理部分和非伦理部分(即通常被归入经济学的部分),让局面变得更加一团糟的是,实际上他的批判对象也常常分不清这两部分。
所以在开始我的评论之前,希望读者先读一下我去年的一篇文章《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科学?》,此文对本篇所涉及的问题背景做了较全面的梳理,这样我在这里的工作就可以简化很多。
罗氏首先将功利主义归结为“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这样一条伦理原则,然后将其解读为三层含义,并逐条加以质疑(p.264):
这里的要害是,罗氏混淆了功利主义和福利主义,后者只是功利主义的一个版本,尽管它是人们提到功利主义一词是通常最先想到的版本,当然,你可以在狭义上使用一个名词,只要说明清楚即可,但罗氏在本章显然又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功利主义一词的,因为他甚至将米塞斯都包含了进来,结果就很混乱了。
【我在本篇中将客观价值论定义为:价值在不同个人之间都是可加的,并且每个人的权重相等;将福利主义定义为:基于客观价值论的功利主义。】
假如我们正确区分基于客观价值论的福利主义和基于主观价值论的另一种功利主义(以下姑且简称为主观功利主义),那么上述质疑就容易回答了:首先,最大多数只是福利主义的原则,而主观功利主义要求的是一致同意【这一点罗氏在后面其实也承认了】,所以第一条质疑至少对后者并不成立。
其次,即便对福利主义者,也可以从理论上避免多数人屠杀少数人之类的理论后果,只要将福利定义为长期福利,并采用一种多层次功利权衡方法即可;确实,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曾将功利权衡默认的视为单层次权衡,即,每次评价公共政策时,都是在完全选择空间上进行功利计算,所谓完全选择空间是指,该空间的范围仅受自然律的约束,而不受其他任何人为规范的约束。
但实际上,这不是必须的,功利主义者完全可以采用一种多层次权衡方式,在每个层次上生成一组伦理规则,后者构成了下一层次功利权衡的选择空间,这样,在具体的公共选择问题上,选择空间已经过几层规则的约束,功利计算只须在这个很小的空间上进行。
比如功利主义者可以说,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首先要确立一条规则:任何无辜者的生命都不可被剥夺,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不贯彻这条规则的社会,都离最大多数最大福利的理想非常遥远。【作为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者,他只须接受这一经验事实即可,没有义务从理论上论证为何会如此】
这种多层次权衡可以基于历史经验而进行,比如功利主义者可以罗列出所有被考察过的社会,评估每个的总体福利水平,做一个排序,然后用统计手段找出那些影响福利水平的因素,并据此而建构出一套多层次规则来拟合统计结果,最终论证:这套规则体系的实施将让一个社会最有机会获得“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不难看出,多层次权衡(more...)
 不过罗氏的批判矛头指向很不明确,把功利主义的各种可能版本混杂在一起批,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不区分其中的伦理部分和非伦理部分(即通常被归入经济学的部分),让局面变得更加一团糟的是,实际上他的批判对象也常常分不清这两部分。
所以在开始我的评论之前,希望读者先读一下我去年的一篇文章《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科学?》,此文对本篇所涉及的问题背景做了较全面的梳理,这样我在这里的工作就可以简化很多。
罗氏首先将功利主义归结为“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这样一条伦理原则,然后将其解读为三层含义,并逐条加以质疑(p.264):
不过罗氏的批判矛头指向很不明确,把功利主义的各种可能版本混杂在一起批,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不区分其中的伦理部分和非伦理部分(即通常被归入经济学的部分),让局面变得更加一团糟的是,实际上他的批判对象也常常分不清这两部分。
所以在开始我的评论之前,希望读者先读一下我去年的一篇文章《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科学?》,此文对本篇所涉及的问题背景做了较全面的梳理,这样我在这里的工作就可以简化很多。
罗氏首先将功利主义归结为“最大多数的最大利益”这样一条伦理原则,然后将其解读为三层含义,并逐条加以质疑(p.264):

 这里的要害是,罗氏混淆了功利主义和福利主义,后者只是功利主义的一个版本,尽管它是人们提到功利主义一词是通常最先想到的版本,当然,你可以在狭义上使用一个名词,只要说明清楚即可,但罗氏在本章显然又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功利主义一词的,因为他甚至将米塞斯都包含了进来,结果就很混乱了。
【我在本篇中将客观价值论定义为:价值在不同个人之间都是可加的,并且每个人的权重相等;将福利主义定义为:基于客观价值论的功利主义。】
假如我们正确区分基于客观价值论的福利主义和基于主观价值论的另一种功利主义(以下姑且简称为主观功利主义),那么上述质疑就容易回答了:首先,最大多数只是福利主义的原则,而主观功利主义要求的是一致同意【这一点罗氏在后面其实也承认了】,所以第一条质疑至少对后者并不成立。
其次,即便对福利主义者,也可以从理论上避免多数人屠杀少数人之类的理论后果,只要将福利定义为长期福利,并采用一种多层次功利权衡方法即可;确实,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曾将功利权衡默认的视为单层次权衡,即,每次评价公共政策时,都是在完全选择空间上进行功利计算,所谓完全选择空间是指,该空间的范围仅受自然律的约束,而不受其他任何人为规范的约束。
但实际上,这不是必须的,功利主义者完全可以采用一种多层次权衡方式,在每个层次上生成一组伦理规则,后者构成了下一层次功利权衡的选择空间,这样,在具体的公共选择问题上,选择空间已经过几层规则的约束,功利计算只须在这个很小的空间上进行。
比如功利主义者可以说,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首先要确立一条规则:任何无辜者的生命都不可被剥夺,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不贯彻这条规则的社会,都离最大多数最大福利的理想非常遥远。【作为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者,他只须接受这一经验事实即可,没有义务从理论上论证为何会如此】
这种多层次权衡可以基于历史经验而进行,比如功利主义者可以罗列出所有被考察过的社会,评估每个的总体福利水平,做一个排序,然后用统计手段找出那些影响福利水平的因素,并据此而建构出一套多层次规则来拟合统计结果,最终论证:这套规则体系的实施将让一个社会最有机会获得“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不难看出,多层次权衡方法同样适用于主观功利主义。
[[Daniel Dennett]]在[[Darwin's Dangerous Idea]]第17章里详细说明了为何单层次的即时功利权衡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类不可能具备做这种权衡所需要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对于功利主义者,功利原则在总体上具有指导性意义,但其实现只能通过对一套多层次规则的不断修补改进,而修改只能是基于经验的。
【注意:我并不是在为功利主义辩护,我也不是功利主义者,更不是福利主义者,我只是在替他们回答罗氏这种最肤浅的质疑。】
再看第二条:为何每个人的福利在计入总福利时,权重都相等?这是福利主义所设定的论证前提,它是先验的,或者用罗氏的话说是公理,不需要论证,当然罗氏可以不同意,但不能以此为质疑对象,罗氏自己不也设定了无须论证的公理吗?比如,为何每个人拥有自有权?为何人与人在伦理规则面前是平等的?
当然,对于主观功利主义者,这条公理是不需要的。
第三条:为何主观满足才是福利度量基准?这里罗氏犯了双重错误,首先,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福利主义者并不以主观满足为价值基准,而是常常悄悄滑向(如果不是明确承认的话)用货币收入或以货币计量的消费额来度量福利,甚至用具体商品(比如粮食、住房、教育、寿命等)的消费数量来度量福利。
其次,对于主观功利主义者,主观价值论是公理,无须论证,罗氏当然可以不接受,但不能要求对方证明自己的公理。
在本章后两个部分(B与C),罗氏将焦点集中到主观派上,这里我忍不住要夸一句,罗氏这一节是我批到现在为止所看到的最佳表现,他确实戳到了帕累托判准和卡尔多-希克斯判准的要害,他对帕累托判准是否价值中立的质疑也是正确的,不过,这两点并不(如他所认为的)足以否决主观功利主义成为自由市场理论基础。
他在三个点上戳中了要害,第一点不太致命:无原则的一致同意可能让社会滑向某种非自由的制度(p.265-266):
这里的要害是,罗氏混淆了功利主义和福利主义,后者只是功利主义的一个版本,尽管它是人们提到功利主义一词是通常最先想到的版本,当然,你可以在狭义上使用一个名词,只要说明清楚即可,但罗氏在本章显然又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功利主义一词的,因为他甚至将米塞斯都包含了进来,结果就很混乱了。
【我在本篇中将客观价值论定义为:价值在不同个人之间都是可加的,并且每个人的权重相等;将福利主义定义为:基于客观价值论的功利主义。】
假如我们正确区分基于客观价值论的福利主义和基于主观价值论的另一种功利主义(以下姑且简称为主观功利主义),那么上述质疑就容易回答了:首先,最大多数只是福利主义的原则,而主观功利主义要求的是一致同意【这一点罗氏在后面其实也承认了】,所以第一条质疑至少对后者并不成立。
其次,即便对福利主义者,也可以从理论上避免多数人屠杀少数人之类的理论后果,只要将福利定义为长期福利,并采用一种多层次功利权衡方法即可;确实,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曾将功利权衡默认的视为单层次权衡,即,每次评价公共政策时,都是在完全选择空间上进行功利计算,所谓完全选择空间是指,该空间的范围仅受自然律的约束,而不受其他任何人为规范的约束。
但实际上,这不是必须的,功利主义者完全可以采用一种多层次权衡方式,在每个层次上生成一组伦理规则,后者构成了下一层次功利权衡的选择空间,这样,在具体的公共选择问题上,选择空间已经过几层规则的约束,功利计算只须在这个很小的空间上进行。
比如功利主义者可以说,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首先要确立一条规则:任何无辜者的生命都不可被剥夺,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不贯彻这条规则的社会,都离最大多数最大福利的理想非常遥远。【作为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者,他只须接受这一经验事实即可,没有义务从理论上论证为何会如此】
这种多层次权衡可以基于历史经验而进行,比如功利主义者可以罗列出所有被考察过的社会,评估每个的总体福利水平,做一个排序,然后用统计手段找出那些影响福利水平的因素,并据此而建构出一套多层次规则来拟合统计结果,最终论证:这套规则体系的实施将让一个社会最有机会获得“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不难看出,多层次权衡方法同样适用于主观功利主义。
[[Daniel Dennett]]在[[Darwin's Dangerous Idea]]第17章里详细说明了为何单层次的即时功利权衡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类不可能具备做这种权衡所需要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对于功利主义者,功利原则在总体上具有指导性意义,但其实现只能通过对一套多层次规则的不断修补改进,而修改只能是基于经验的。
【注意:我并不是在为功利主义辩护,我也不是功利主义者,更不是福利主义者,我只是在替他们回答罗氏这种最肤浅的质疑。】
再看第二条:为何每个人的福利在计入总福利时,权重都相等?这是福利主义所设定的论证前提,它是先验的,或者用罗氏的话说是公理,不需要论证,当然罗氏可以不同意,但不能以此为质疑对象,罗氏自己不也设定了无须论证的公理吗?比如,为何每个人拥有自有权?为何人与人在伦理规则面前是平等的?
当然,对于主观功利主义者,这条公理是不需要的。
第三条:为何主观满足才是福利度量基准?这里罗氏犯了双重错误,首先,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福利主义者并不以主观满足为价值基准,而是常常悄悄滑向(如果不是明确承认的话)用货币收入或以货币计量的消费额来度量福利,甚至用具体商品(比如粮食、住房、教育、寿命等)的消费数量来度量福利。
其次,对于主观功利主义者,主观价值论是公理,无须论证,罗氏当然可以不接受,但不能要求对方证明自己的公理。
在本章后两个部分(B与C),罗氏将焦点集中到主观派上,这里我忍不住要夸一句,罗氏这一节是我批到现在为止所看到的最佳表现,他确实戳到了帕累托判准和卡尔多-希克斯判准的要害,他对帕累托判准是否价值中立的质疑也是正确的,不过,这两点并不(如他所认为的)足以否决主观功利主义成为自由市场理论基础。
他在三个点上戳中了要害,第一点不太致命:无原则的一致同意可能让社会滑向某种非自由的制度(p.265-266):
 确实有可能,如果不用某些基础规则对可表决事项作出限制的话(罗氏所谓“零起点”大概就是这意思),即便社会原本在自由制度中,也可能经过一系列表决而滑入非自由制度,在单层次即时权衡模式下,这个窗口是永远开放着的,但这问题可以通过前面说的多层次权衡模式来解决,将某些事情规定为不可表决的,这样相关提案就不会进入表决机制。
或者,我们可以用霍姆斯式的话来回答这一质疑:假如全体一致同意决定走向地狱,还有谁能拦得住呢?毕竟任何制度都不可能确保自由永存,这不是否决一种制度的充分理由。
第二点是帕累托判准被修正为卡尔多-希克斯判准时所出现的漏洞(p.266):
确实有可能,如果不用某些基础规则对可表决事项作出限制的话(罗氏所谓“零起点”大概就是这意思),即便社会原本在自由制度中,也可能经过一系列表决而滑入非自由制度,在单层次即时权衡模式下,这个窗口是永远开放着的,但这问题可以通过前面说的多层次权衡模式来解决,将某些事情规定为不可表决的,这样相关提案就不会进入表决机制。
或者,我们可以用霍姆斯式的话来回答这一质疑:假如全体一致同意决定走向地狱,还有谁能拦得住呢?毕竟任何制度都不可能确保自由永存,这不是否决一种制度的充分理由。
第二点是帕累托判准被修正为卡尔多-希克斯判准时所出现的漏洞(p.266):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卡尔多-希克斯判准其实部分的滑向了客观价值论,因为它的所谓“充分补偿”若是按主观价值的“充分”,那么这件事情完全可以由个人之间的自愿交易来完成,而不必成为需要由该判准来进行功利权衡的公共决策或法官裁决,所以实际上运用该判准时,都是以市价等客观价值来衡量补偿是否充分的。
可是,既然客观价值论是可接受的,那又何必大费周折的从帕累托判准修正出一个新判准呢,直接金钱收益衡量社会总福利不就行了?
不过这一质疑也是可以回答的,办法还是多层次权衡,我的提议是:将卡尔多-希克斯判准限制于那些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公共选择的事情上,比如涉及某类行为的权利边界尚未被法律划定(可能是因为此类行为是新出现的,而行为空间在最近才变得拥挤起来),此时为了给这些行为划定边界,必须做出某种权衡。
或者有人可能会把条件放得更宽:只要是更高层次上的规则允许其成为公共选择的那些事情上,在作出选择时将适用卡尔多-希克斯判准,比如在进入战争状态或其他公共危机状态时,政府可以征用某些私人财产来获得所需战争资源,此时补偿标准的制定便适用卡尔多-希克斯判准;当然,你或许认为这样的标准太宽了,但它至少能够自圆。
第三点最为致命,罗氏在评论米塞斯时(通过价格管制这个例子)指出(当然,罗氏表述的没这么清楚,但假如你读过我去年那篇文章,应不难看出这层意思):若严格遵守主观价值论和价值中立原则,帕累托判准其实毫无用处,而要让它变得有用,它就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p.270):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卡尔多-希克斯判准其实部分的滑向了客观价值论,因为它的所谓“充分补偿”若是按主观价值的“充分”,那么这件事情完全可以由个人之间的自愿交易来完成,而不必成为需要由该判准来进行功利权衡的公共决策或法官裁决,所以实际上运用该判准时,都是以市价等客观价值来衡量补偿是否充分的。
可是,既然客观价值论是可接受的,那又何必大费周折的从帕累托判准修正出一个新判准呢,直接金钱收益衡量社会总福利不就行了?
不过这一质疑也是可以回答的,办法还是多层次权衡,我的提议是:将卡尔多-希克斯判准限制于那些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公共选择的事情上,比如涉及某类行为的权利边界尚未被法律划定(可能是因为此类行为是新出现的,而行为空间在最近才变得拥挤起来),此时为了给这些行为划定边界,必须做出某种权衡。
或者有人可能会把条件放得更宽:只要是更高层次上的规则允许其成为公共选择的那些事情上,在作出选择时将适用卡尔多-希克斯判准,比如在进入战争状态或其他公共危机状态时,政府可以征用某些私人财产来获得所需战争资源,此时补偿标准的制定便适用卡尔多-希克斯判准;当然,你或许认为这样的标准太宽了,但它至少能够自圆。
第三点最为致命,罗氏在评论米塞斯时(通过价格管制这个例子)指出(当然,罗氏表述的没这么清楚,但假如你读过我去年那篇文章,应不难看出这层意思):若严格遵守主观价值论和价值中立原则,帕累托判准其实毫无用处,而要让它变得有用,它就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p.270):
 【再表扬一遍:上面这段话是罗斯巴德这本书里头脑最清楚、论证最有力的一段。】
正如我在旧文中所指出,若将帕累托判准里的worse off理解为实际利益受损,并且严格遵守主观价值论的话,那么多人世界中的任何行为都无法被判定为帕累托改进,哪怕是纯粹的个人私事(比如我摸一下自己的鼻子)和个人间的自愿交易,只要有一个人说:我就是看不惯这样的事情,一看见(或一听说)就难受,那就不是帕累托改进了。
所以,要让帕累托判准变得有用,就必须将其中的worse off理解为法定权益受损,但这样就必须首先规定什么是权利,而规定权利的过程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最起码,“权利主体应是个人”“权利应得到保护”之类的规则,就包含了价值判断,“人身免遭伤害是当然权利”“每个人拥有同等人身权利”更包含了价值判断。
但是,尽管从完全的价值中立原则不可能为支持任何制度(更不要说自由市场制度)建立理论基础,可是“最大程度的价值中立”仍是可能的,这意味着这套理论所需要的价值共识是最少的,而基于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学正是这样一套理论,它只要求人们就最基础的伦理规则达成价值共识,并据此划定权利边界,而无须对边界之内发生的事情做任何共同的价值判断。
并且,在如此划定权利边界之后,经济学家确实能够运用(修正后的)帕累托判准对某些公共政策作出“价值中立”的优劣判断,只是这一价值中立是在较低层次上的中立,而从更高的层次上看,它是非中立的,因为它已假定了一个非中立的前提:权利应得到保护,权利边界之内的利益才值得被政策评价所考虑。
同样,解决困境的仍是一种多层次权衡:首先权衡划定权利的制度,然后在制度所构造和限定的选择空间内权衡政策。
【再表扬一遍:上面这段话是罗斯巴德这本书里头脑最清楚、论证最有力的一段。】
正如我在旧文中所指出,若将帕累托判准里的worse off理解为实际利益受损,并且严格遵守主观价值论的话,那么多人世界中的任何行为都无法被判定为帕累托改进,哪怕是纯粹的个人私事(比如我摸一下自己的鼻子)和个人间的自愿交易,只要有一个人说:我就是看不惯这样的事情,一看见(或一听说)就难受,那就不是帕累托改进了。
所以,要让帕累托判准变得有用,就必须将其中的worse off理解为法定权益受损,但这样就必须首先规定什么是权利,而规定权利的过程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最起码,“权利主体应是个人”“权利应得到保护”之类的规则,就包含了价值判断,“人身免遭伤害是当然权利”“每个人拥有同等人身权利”更包含了价值判断。
但是,尽管从完全的价值中立原则不可能为支持任何制度(更不要说自由市场制度)建立理论基础,可是“最大程度的价值中立”仍是可能的,这意味着这套理论所需要的价值共识是最少的,而基于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学正是这样一套理论,它只要求人们就最基础的伦理规则达成价值共识,并据此划定权利边界,而无须对边界之内发生的事情做任何共同的价值判断。
并且,在如此划定权利边界之后,经济学家确实能够运用(修正后的)帕累托判准对某些公共政策作出“价值中立”的优劣判断,只是这一价值中立是在较低层次上的中立,而从更高的层次上看,它是非中立的,因为它已假定了一个非中立的前提:权利应得到保护,权利边界之内的利益才值得被政策评价所考虑。
同样,解决困境的仍是一种多层次权衡:首先权衡划定权利的制度,然后在制度所构造和限定的选择空间内权衡政策。
(应景口水文,没啥看头)
苹果的未来
辉格
2012年9月18日
众粉丝期盼已久iPhone5终于在上周的发布会上揭晓,本周起将在各地上市,苹果的股价也随之而被推到了新高;不过其中过程颇值得玩味,新苹果发布之初,股价一度大跌,因为业内行家普遍觉得让人苦等了一年的这代新品并无多少新意,而除了手机,苹果也没拿出其他能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
可是股价下跌势头只维持了半天,当投资者发现消费者热情并未受评论影响,似乎并不介意新苹果的平淡表现,股价很快又开始反弹,几天后当预订数字显示新苹果早期销量很可能超出4S时,股价更突破700美元大关创出(more...)
#第25章#
本章,罗氏将其理论运用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他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何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无论是入侵还是反入侵)都是罪恶的,只有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国内革命战争可能是正当的。
我原本以为,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罗氏大概不会在乎国家主权边界之类事情,可让我惊奇的是,通过一串让人眼花缭乱的“论证”,他居然得出了一套类似于“主权至上互不侵犯”的国际法原则,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论证的。
先看罗氏如何论证为何国内革命可能是正当的,而国际战争则不可能(p.255):
他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因为革命者与其敌人同处一个地理空间,为避免自伤,只得采用精确杀伤武器,因而容易防止伤及无辜,而国际战争则做不到(p.254-255):
这条理由很可笑,稍有点历史常识就知道,无论古今,除非有意识屠杀平民,国家间正规战争伤及无辜的程度都远远小于改朝换代的暴动、起义和革命,而且越到晚近,军队组织和武器技术越进步,正规战争避免伤及无辜的能力也越强。
对此,罗氏提出的论证仅仅是:弓箭步枪等传统武器容易瞄准,而大炮轰炸机核武器等现代武器则更盲目;可是传统武器可不止这两种,战术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大规模纵火、决堤灌水、驱赶畜群、长期围城、坚壁清野、人肉盾牌,都是常用战术,每种都涉及对无辜平民的大规模侵犯。
而且,伤害无辜的因素主要不在武器,组织与后勤方式才是关键,正规军虽然也有军纪问题、也会就地寻找给养,但和革命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暴动起义者都是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而且它的成功动力往往就来自对沿路平民生存条件的破坏,让大批失去生计的平民加入队伍。
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近现代正规战争和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革命的人口影响,就再清楚不过了,后者在短短几十年内消灭1/3、1/2、甚至2/3人口,都不在话下,而近代欧洲的连绵战火加起来都比不上其中之一,更不用说美国最近发动的几次战争了,其打击精度和避免平民伤亡的能力,使得平民伤亡与同期国内暴乱相比只是零头。
再看罗氏第二条理由(p.255):
空口胡说,请问罗粉能否举出一个例子,国内革命的经费都是个人自愿捐助的?
再来看罗氏如何为国际关系设定伦理标准。
此前几章罗氏已反复强调,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犯罪集团,既然如此,谈论他们之间的行为是否正当有意义吗?罗氏认为有,因为虽然都是犯罪,但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程度不同,而他的国际伦理标准就是:尽可能降低国家对个人的侵犯程度(p.256):
这听上去不错,可是,不知出于何种神奇逻辑,罗氏由此推出了“应完全避免战争”这一结论(p.256):
注意,罗氏在此处令人意外的采取了一种功利主义立场,既然他认为可以“减少国家侵入个人的领域”和将“侵入限定在尽可能小的程度”,那么他就承认了两项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是可以比较大小的,这样,按他的侵犯最小化原则,当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侵犯中二选一,就该选侵犯程度较小的那种。
比如,A国政府对其国民实施程度为9的持续侵犯,B国政府对其国民实施程度为1(more...)
 他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因为革命者与其敌人同处一个地理空间,为避免自伤,只得采用精确杀伤武器,因而容易防止伤及无辜,而国际战争则做不到(p.254-255):
他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因为革命者与其敌人同处一个地理空间,为避免自伤,只得采用精确杀伤武器,因而容易防止伤及无辜,而国际战争则做不到(p.254-255):
 这条理由很可笑,稍有点历史常识就知道,无论古今,除非有意识屠杀平民,国家间正规战争伤及无辜的程度都远远小于改朝换代的暴动、起义和革命,而且越到晚近,军队组织和武器技术越进步,正规战争避免伤及无辜的能力也越强。
对此,罗氏提出的论证仅仅是:弓箭步枪等传统武器容易瞄准,而大炮轰炸机核武器等现代武器则更盲目;可是传统武器可不止这两种,战术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大规模纵火、决堤灌水、驱赶畜群、长期围城、坚壁清野、人肉盾牌,都是常用战术,每种都涉及对无辜平民的大规模侵犯。
而且,伤害无辜的因素主要不在武器,组织与后勤方式才是关键,正规军虽然也有军纪问题、也会就地寻找给养,但和革命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暴动起义者都是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而且它的成功动力往往就来自对沿路平民生存条件的破坏,让大批失去生计的平民加入队伍。
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近现代正规战争和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革命的人口影响,就再清楚不过了,后者在短短几十年内消灭1/3、1/2、甚至2/3人口,都不在话下,而近代欧洲的连绵战火加起来都比不上其中之一,更不用说美国最近发动的几次战争了,其打击精度和避免平民伤亡的能力,使得平民伤亡与同期国内暴乱相比只是零头。
再看罗氏第二条理由(p.255):
这条理由很可笑,稍有点历史常识就知道,无论古今,除非有意识屠杀平民,国家间正规战争伤及无辜的程度都远远小于改朝换代的暴动、起义和革命,而且越到晚近,军队组织和武器技术越进步,正规战争避免伤及无辜的能力也越强。
对此,罗氏提出的论证仅仅是:弓箭步枪等传统武器容易瞄准,而大炮轰炸机核武器等现代武器则更盲目;可是传统武器可不止这两种,战术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大规模纵火、决堤灌水、驱赶畜群、长期围城、坚壁清野、人肉盾牌,都是常用战术,每种都涉及对无辜平民的大规模侵犯。
而且,伤害无辜的因素主要不在武器,组织与后勤方式才是关键,正规军虽然也有军纪问题、也会就地寻找给养,但和革命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暴动起义者都是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而且它的成功动力往往就来自对沿路平民生存条件的破坏,让大批失去生计的平民加入队伍。
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近现代正规战争和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革命的人口影响,就再清楚不过了,后者在短短几十年内消灭1/3、1/2、甚至2/3人口,都不在话下,而近代欧洲的连绵战火加起来都比不上其中之一,更不用说美国最近发动的几次战争了,其打击精度和避免平民伤亡的能力,使得平民伤亡与同期国内暴乱相比只是零头。
再看罗氏第二条理由(p.255):
 空口胡说,请问罗粉能否举出一个例子,国内革命的经费都是个人自愿捐助的?
再来看罗氏如何为国际关系设定伦理标准。
此前几章罗氏已反复强调,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犯罪集团,既然如此,谈论他们之间的行为是否正当有意义吗?罗氏认为有,因为虽然都是犯罪,但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程度不同,而他的国际伦理标准就是:尽可能降低国家对个人的侵犯程度(p.256):
空口胡说,请问罗粉能否举出一个例子,国内革命的经费都是个人自愿捐助的?
再来看罗氏如何为国际关系设定伦理标准。
此前几章罗氏已反复强调,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犯罪集团,既然如此,谈论他们之间的行为是否正当有意义吗?罗氏认为有,因为虽然都是犯罪,但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程度不同,而他的国际伦理标准就是:尽可能降低国家对个人的侵犯程度(p.256):
 这听上去不错,可是,不知出于何种神奇逻辑,罗氏由此推出了“应完全避免战争”这一结论(p.256):
这听上去不错,可是,不知出于何种神奇逻辑,罗氏由此推出了“应完全避免战争”这一结论(p.256):
 注意,罗氏在此处令人意外的采取了一种功利主义立场,既然他认为可以“减少国家侵入个人的领域”和将“侵入限定在尽可能小的程度”,那么他就承认了两项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是可以比较大小的,这样,按他的侵犯最小化原则,当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侵犯中二选一,就该选侵犯程度较小的那种。
比如,A国政府对其国民实施程度为9的持续侵犯,B国政府对其国民实施程度为1的持续侵犯,若B对A发动战争,有望推翻A国政府并在A国实施B的制度,将A国国民所受持续侵犯程度降至1,而为了完成这场战争,B国须在5年内将对本国国民的侵犯程度提高到3,再假设两国人口相当,那么按罗氏理论,这场战争岂不是正当的了?
当然有人会说,凭啥让B国国民承担牺牲去拯救A国国民?那就让我们再修改一下前提条件:假如A国目前的制度和社会状况让B国始终面临着遭遇A国入侵或被其国内革命殃及的危险之中,为了预防这种风险而需要的国防开支,迫使B国政府维持高税率,使其对国民的侵犯程度长期高达2,而不是本该有的1,那么,B国通过战争来摆脱上述风险和负担,顺便拯救了A国国民,岂不是正当的?
令人失望的是,罗氏对此的论证极为苍白,他对这种战争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只是:那会增加税收侵犯和造成无辜平民伤亡,也就是说,它是有成本的,可是既然你采取了功利主义标准,那就应该算净收益,而不能因为某一选项是有成本的就排除它,实际上这种时候任何选项都是有成本的。
似乎是为了对此尴尬漏洞贴膏药,罗氏提出了一个奇妙观点(p.255-256):
注意,罗氏在此处令人意外的采取了一种功利主义立场,既然他认为可以“减少国家侵入个人的领域”和将“侵入限定在尽可能小的程度”,那么他就承认了两项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是可以比较大小的,这样,按他的侵犯最小化原则,当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侵犯中二选一,就该选侵犯程度较小的那种。
比如,A国政府对其国民实施程度为9的持续侵犯,B国政府对其国民实施程度为1的持续侵犯,若B对A发动战争,有望推翻A国政府并在A国实施B的制度,将A国国民所受持续侵犯程度降至1,而为了完成这场战争,B国须在5年内将对本国国民的侵犯程度提高到3,再假设两国人口相当,那么按罗氏理论,这场战争岂不是正当的了?
当然有人会说,凭啥让B国国民承担牺牲去拯救A国国民?那就让我们再修改一下前提条件:假如A国目前的制度和社会状况让B国始终面临着遭遇A国入侵或被其国内革命殃及的危险之中,为了预防这种风险而需要的国防开支,迫使B国政府维持高税率,使其对国民的侵犯程度长期高达2,而不是本该有的1,那么,B国通过战争来摆脱上述风险和负担,顺便拯救了A国国民,岂不是正当的?
令人失望的是,罗氏对此的论证极为苍白,他对这种战争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只是:那会增加税收侵犯和造成无辜平民伤亡,也就是说,它是有成本的,可是既然你采取了功利主义标准,那就应该算净收益,而不能因为某一选项是有成本的就排除它,实际上这种时候任何选项都是有成本的。
似乎是为了对此尴尬漏洞贴膏药,罗氏提出了一个奇妙观点(p.255-256):
 而且居然赞赏起了主权独立原则(p.257):
而且居然赞赏起了主权独立原则(p.257):
 可是,你不是说国家都是犯罪集团吗?犯罪集团的主权为何值得尊重?犯罪集团之间擅自划分的分赃边界怎么会获得伦理地位?而且还是“庄严的”?各犯罪集团将其犯罪活动限制在各自边界之内,为何就会让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最小化?一个极权政府,若无入侵和外来颠覆之虞,不是更能安心的压迫国民吗?被严格尊重的主权边界,不是削弱了制度竞争的强度和效果吗?当前的朝鲜和古巴不正是如此?
在上一章里,罗氏刚刚嘲讽了有限政府的说法,认为政府天然的具有扩张权力、加重对个人侵犯的倾向,一旦政府存在,指望其权力受到限制是“虚幻的乌托邦”想法,可现在,罗氏怎么却指望一个政府会老老实实的将自己的权力限制在国界线之内?难道国界线比宪法更能有效的阻止权力扩张?即便是弱小如芬兰的国界线,也能阻止强大如苏联的权力扩张?若阻止不了呢?原本还算自由的芬兰国民就活该被奴役?
接着,罗氏将其反战原则推到极致,不仅入侵他国是不正当的,遭遇入侵时的防卫战争也是不正当的,因为防卫会拖延战争并提高战争烈度,加重双方国民负担,不如对比一下实力大小,注定要输的那方赶紧认输了事(p.256):
可是,你不是说国家都是犯罪集团吗?犯罪集团的主权为何值得尊重?犯罪集团之间擅自划分的分赃边界怎么会获得伦理地位?而且还是“庄严的”?各犯罪集团将其犯罪活动限制在各自边界之内,为何就会让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最小化?一个极权政府,若无入侵和外来颠覆之虞,不是更能安心的压迫国民吗?被严格尊重的主权边界,不是削弱了制度竞争的强度和效果吗?当前的朝鲜和古巴不正是如此?
在上一章里,罗氏刚刚嘲讽了有限政府的说法,认为政府天然的具有扩张权力、加重对个人侵犯的倾向,一旦政府存在,指望其权力受到限制是“虚幻的乌托邦”想法,可现在,罗氏怎么却指望一个政府会老老实实的将自己的权力限制在国界线之内?难道国界线比宪法更能有效的阻止权力扩张?即便是弱小如芬兰的国界线,也能阻止强大如苏联的权力扩张?若阻止不了呢?原本还算自由的芬兰国民就活该被奴役?
接着,罗氏将其反战原则推到极致,不仅入侵他国是不正当的,遭遇入侵时的防卫战争也是不正当的,因为防卫会拖延战争并提高战争烈度,加重双方国民负担,不如对比一下实力大小,注定要输的那方赶紧认输了事(p.256):
 连防御战争都反对,这一点在这段引文里表达的比较暧昧,不过,在罗氏1973年出版的[[For a New Liberty]]一书第14章War and Foreign Policy里,可以看的更清楚,因为那章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观点,而本章没有实例;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39年苏芬战争,罗氏为苏联的入侵做了许多辩护,并认为芬兰不应抵抗。
可是,假如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不正当的,那么,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比如香港,若被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征服,国家对个人的侵犯程度难道不是大幅提高了吗?这又如何与罗氏的侵犯最小化原则相容?
总结起来,罗氏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托尔斯泰式的无条件反战主义,反对任何战争,包括防卫战争,也反对任何国防开支,可是,只要现实中存在一个奉行侵略性政策的国家,这套理论就毫无用处,对于如何实现和平毫无提示,对罗氏自己所设定的国际关系目标:国家对个人侵犯最小化,也毫无助益。
从理论上看,罗氏的反战思想只是其无政府主义体系的一个旁支,不过,在他的日常政治活动和言论中,反战其实占了很大的份额,他所创建的组织、办的刊物,把很大一部分资源和注意力用在了这上面,为此不惜与左派反战者结成联盟,假如你只看他的政治活动和政策主张的话,那活脱脱就是另一个乔姆斯基。
连防御战争都反对,这一点在这段引文里表达的比较暧昧,不过,在罗氏1973年出版的[[For a New Liberty]]一书第14章War and Foreign Policy里,可以看的更清楚,因为那章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观点,而本章没有实例;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39年苏芬战争,罗氏为苏联的入侵做了许多辩护,并认为芬兰不应抵抗。
可是,假如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不正当的,那么,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比如香港,若被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征服,国家对个人的侵犯程度难道不是大幅提高了吗?这又如何与罗氏的侵犯最小化原则相容?
总结起来,罗氏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托尔斯泰式的无条件反战主义,反对任何战争,包括防卫战争,也反对任何国防开支,可是,只要现实中存在一个奉行侵略性政策的国家,这套理论就毫无用处,对于如何实现和平毫无提示,对罗氏自己所设定的国际关系目标:国家对个人侵犯最小化,也毫无助益。
从理论上看,罗氏的反战思想只是其无政府主义体系的一个旁支,不过,在他的日常政治活动和言论中,反战其实占了很大的份额,他所创建的组织、办的刊物,把很大一部分资源和注意力用在了这上面,为此不惜与左派反战者结成联盟,假如你只看他的政治活动和政策主张的话,那活脱脱就是另一个乔姆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