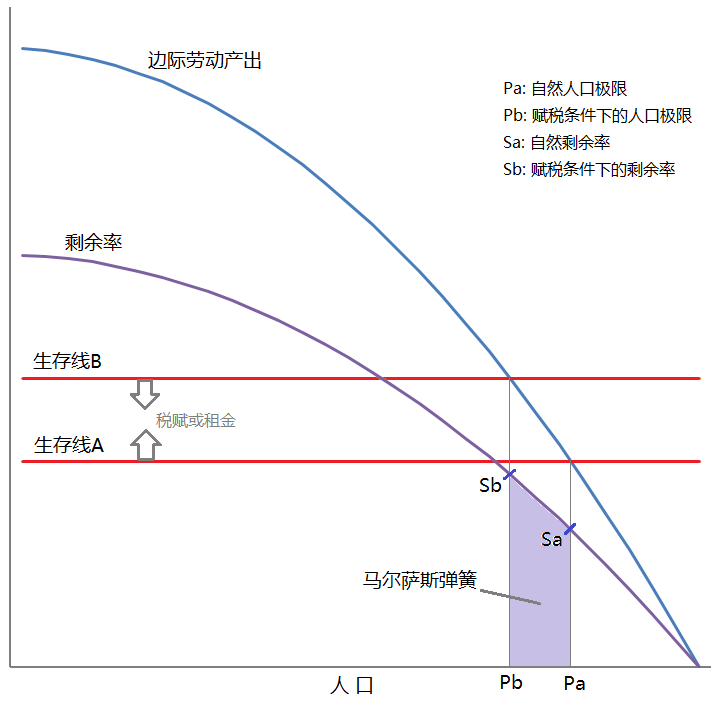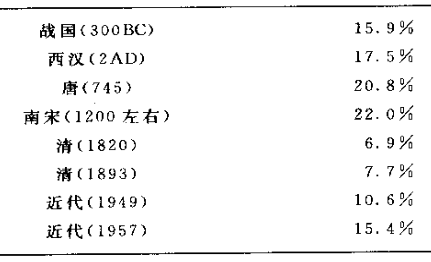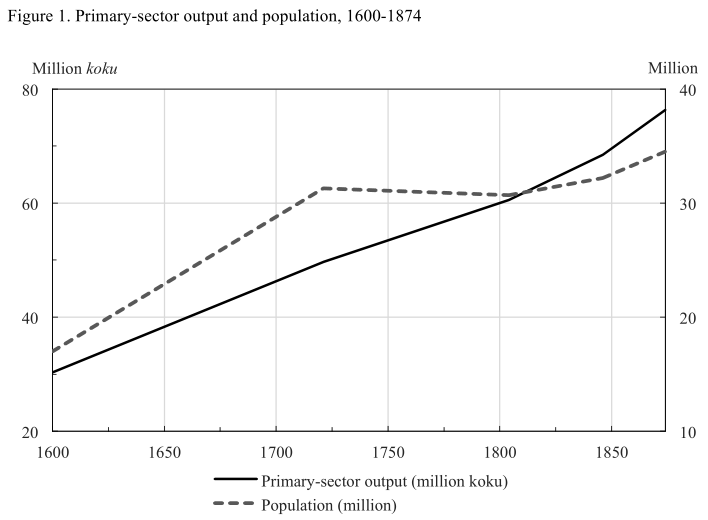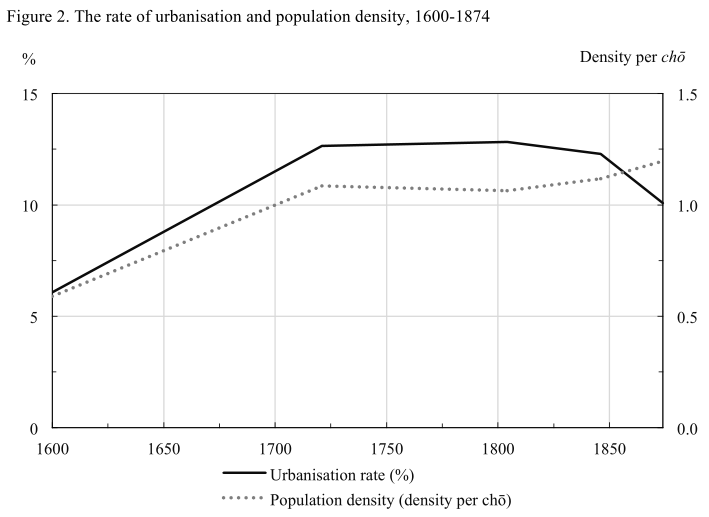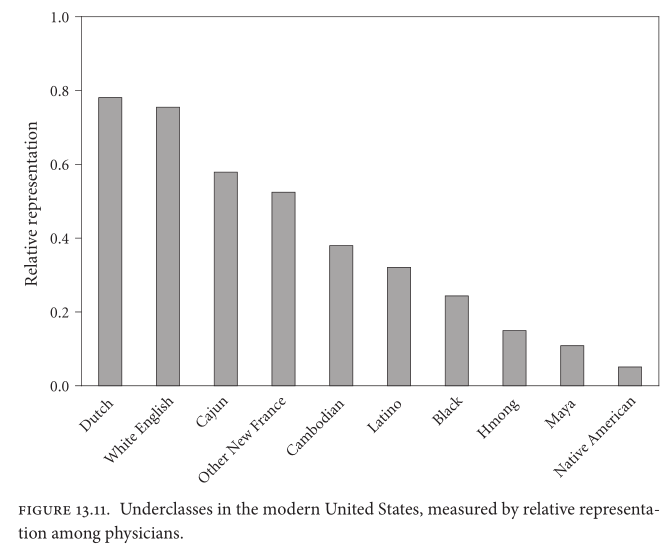权力积木#2:信息与控制
辉格
2015年12月3日
一个广域国家的统治者面临各种技术难题,比如在前文已讨论过的领地安全问题中,为了对入侵和叛乱做出及时反应,他不仅需要机动优势,还需要以5-10倍于行军的速度传送情报,而即便如此,当疆域非常广阔时,也必须在多个据点驻扎军队,而不能集中于一点;行政系统也是如此,为实现有效治理,广袤领地须划分成若干单元,分别派驻官吏。
更一般而言,当统治团队膨胀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它本身也受制于邓巴局限,因而只能建立层级组织,假设按每个上级单元控制20个下级单元(1:20已经是非常扁平的结构,只能实现较弱的控制,有关这一点我以后会展开讨论),那么,从一两百人的熟人小社会到数千万人的帝国,就至少需要四个层级。
然而,一旦建立层级组织,就会面临所有委托-代理关系中都存在的激励和控制难题,瞒上欺下,职权滥用,目标偏离,推诿责任,沟通不畅,协调失灵,以及最危险的背叛和分离;最高权力者总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克服这些障碍,那些或多或少管用的办法就被延用下来,构成了我们在历史中所见到的种种政体结构、制度安排和组织工具。
防止叛乱的一种方法是多线控制,将维持下级单元运行所需职能加以分割,交给不同人掌管,并通过不同的层级系统加以控制,使得其中每个都无法单独行动,从而剥夺下级单元的独立性;例如,由将领掌握军队指挥权,由行政系统负责粮草供给,这样,叛军很快会因失去粮草而陷入瘫痪。
另一种方法是阻止上下级官员之间发展私人效忠关系,缩短任期、频繁调动、任职回避、把奖励和提拔权限保留在高层,都是出于这一目的;另外,在重臣身边安插耳目,派出巡回监察官,维持多个独立情报来源,要求同级官员分头汇报情况以便核查真伪虚实,都是常见的做法。
强化控制的终极手段,是直接发号施令,让官员忙于执行频繁下达的任务而无暇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让他们看不清系统的整体运营机制因而无法打自己的小算盘;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有句名言:(大意)“每天起床都要等着别人告诉他今天要做什么的人,肯定是农奴。”当控制强化到极致时,臣僚便成了君主的奴仆。
当然,这些做法都是有代价的,多线控制削弱了下级单元的独立应变能力,面对突发危机时,协调障碍可能是致命的;在古代的组织条件下,消除个人效忠也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点在历史上已屡屡得到证明,较近的例子是,湘军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曾国藩等人所建立的个人效忠网络,北洋新军相对于绿营清军的一大优势也是个人效忠。
然而,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前提:高速通信;多线控制下,军队和粮草都可囤在前线基地,但指令必须由上层发出,平时被刻意隔离的几套体系,离开中央指挥就难以协调行动;同样,有效的监视、巡察、考核、奖惩,也都依赖于快速高效的情报传递,直接遥控指挥更需要近乎于实时的通信能力;正因此,所有帝国都建立了效率远远超出同时代民用水平的通信系统。
自从定居之后,便有了入侵警报机制,发现盗贼时,人们以鸣锣呼喊等方式通知邻居,循声追捕(hue and cry)是中世纪英格兰社区对付盗贼的惯常方法,只要盗贼还没离开视线,所有目击者都有义务追呼,hue的拉丁词源可能是hutesium(号角),和铜锣一样,号角也是用于警报的通信工具。
当部落扩大到多个村寨时,功率更大的鼓就被用于远程警报,流行于百越民族的铜鼓,可将信号传出几公里乃至十几公里,经接力传递更可达上百公里,由于铜鼓的覆盖范围大,也被长老和酋长们用于召集民众,因而成为权威和共同体凝聚力的象征,类似于欧洲市镇的钟楼;钟鼓楼也是古代中国行政城市的标准配置,其象征意义毋庸置疑。
非洲人将鼓的通信功能发挥到了极致,通常,鼓只能通过节奏变化编码少量信息,带宽十分有限,但西非人凭借可调音高的沙漏状皮带鼓创造了一种能够传递丰富信息的鼓语(talking drum),用音调变化模拟语音流,效果类似于闭着嘴用鼻音说汉语。
因为班图语和汉语一样也是声调语言(tonal language),这样的模拟确实可行,当然,去掉元辅音丢失了大量信息,听者很难猜到在说什么,特别是失去当面对话中的手势体态环境等辅助信息之后,为此,鼓语者会附加大量冗余来帮助听者还原:重复、排比、修饰,把单词拉长成句子,插入固定形式的惯用短语来提示上下文,等等,长度加长到所模拟语音的五六倍。
鼓语不仅被用于在村庄之间传讯,也被大量用于私人生活,召唤家人回家,通知有客来访,谈情说爱,或只是闲聊,在20世纪上半叶鼓语还盛行时,人人都有一个鼓语名;不过,自发形成的鼓语毕竟不够精确,难以满足军事和行政需要,阿散蒂(Ashanti)和约鲁巴(
标签:历史 | 国家 | 技术 | 权力积木 | 通信

 订阅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