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ban:1871281*}
评价:★★★★☆
简评:不错,篇幅适中且有内容,理论功底也可以,适合希望大致了解者
评价:★★★★☆
简评:不错,篇幅适中且有内容,理论功底也可以,适合希望大致了解者
题:平面内,由若干相邻全等正六边形组成蜂窝网络,其中部分蜂窝为深色,其余为浅色,问:深色蜂窝如何分布可满足如下条件?此时深浅色蜂窝比例为多少?
1)每个深色蜂窝被6个浅色蜂窝围绕,
2)不可能将任何浅色蜂窝改为深色,而继续满足条件(1)。
题目不难,大概算初中程度,不过之前确实没想过,昨天读施坚雅(G.W. Skinner)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才遇到这问题,而且答案与直觉还有点出入。
施坚雅在该书中提出的蜂窝模型(姑且这么叫吧)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不过读了原著还是发现比以前听说和想象的更精致巧妙的多,是社会结构自组织(或曰自发秩序)的一个精彩案例,该模型中基本的单位是“基层市场”(蜂窝),其标准配置是1个基层集镇和围绕它18个村庄,这些村庄组成两个环,内环6个,外环12个,从集镇辐射出6条小路,通往这些村庄。
蜂窝比较简单,但蜂窝之间的组合就颇为复杂,面临两个结构问题,首先,相邻蜂窝之间会发生分化,其中一些集镇会升级为二级集镇,为周边市场提供后者无法提供的市场功能,如批发和中介服务、需求量较小的商品和服务等,典型的二级集镇由6个基层集镇所围绕,它们共同组成一个二级市场,问题是:如何围绕法?具体的空间分布是怎样的?(这就是上面的题目所问的)
其次,传统集市大多不是每天开市,(m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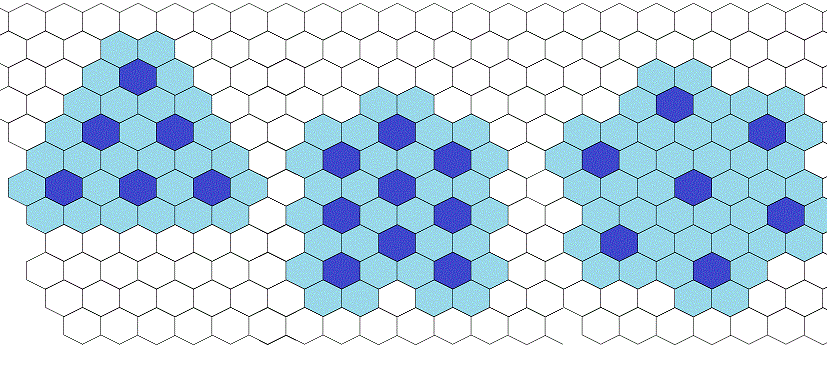
许多人大概都会注意到,某些商品,特别是以份为单位的零售食品,其价格波动很有趣:当成本上升而不得不提价时,通常不是每份的价格上涨,而是份量减少,比如近年来通涨凶猛,每碗拉面的价格涨幅却较小,涨价频率也很低,结果是拉面里的牛肉明显的越来越少,让我这种爱吃肉的很不爽,现在几乎戒吃拉面了。
我把这种价格现象称为“名义价格刚性”,不过一直停留在直觉水平,没找过专门的研究,刚刚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里惊喜的读到一个定量案例:威尼斯1570s-1580s年代,面包重量与小麦价格成高度严格的反比关系,下图取自该书第一卷第二章(p.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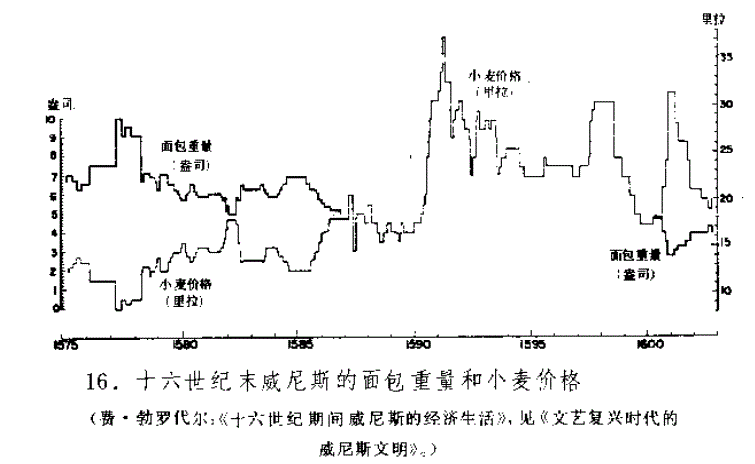 从消费者的便利性考虑,面包重量应该与其消费量成某种比例关系,比如一个大号面包差不多够一个成年人吃一天,而重量的随机变动显然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便,所以只能认为,一定有某种顽固的心理机制,使得他们宁愿承担这种不便,而排斥那些固定重量而让价格浮动的面包厂商。
我还没想出其中道理。
从消费者的便利性考虑,面包重量应该与其消费量成某种比例关系,比如一个大号面包差不多够一个成年人吃一天,而重量的随机变动显然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便,所以只能认为,一定有某种顽固的心理机制,使得他们宁愿承担这种不便,而排斥那些固定重量而让价格浮动的面包厂商。
我还没想出其中道理。这两天在看年鉴派(Annales School)大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法国农村史》(French Rural History),冒出一个念头,耕作技术或许在农业社会的制度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如多圃轮作制(multi-field rotation)很可能强化巩固了西欧封建制度(虽然未必是导致了它的起源),而以三圃制(three-field rotation)的瓦解和圈地运动(Enclosure)为核心内容的农业革命,最终摧毁了封建制的基础。
轮作(crop rotation)是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抵抗害虫和病菌的农业技术,(粗略的说)在中国,实现方法是复种轮作(multiple cropping),而在欧洲,主要方式是多圃轮作,中世纪尤以三圃制为主,两种技术在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是:前者兼容于分散的自耕农模式,而后者必须有较大规模的庄园制度作为支持。
昨天在豆瓣上看到一个有趣的话题,赵行德同学对钟表首先出现在西欧而非中国提出了他的解释,原文较长,大致意思是:航海定位需要推动了天文学研究,而天文观测需要精确计时,于是大航海的强烈需求最终推动了钟表技术的进步。
这个说法有点道理,但我不大同意。
我对钟表技术发展所知不多,主要得自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发现者》(The Discoverers)中的介绍,他花了两编六章的篇幅叙述了计时技术的历史,如此不吝篇幅,有两个原因,1)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这是该书主题)上,时间观念的演变是一个重要方面,2)(more...)
小橘子问我“对交易成本、制度经济学、科斯、布坎南、阿尔钦、威廉姆森有何评价”,这问题对我本人挺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的一次思想转变。
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我都挺喜欢的,特别是在04年之前,制度是我愿意终生关注的课题之一,而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引入是很大的突破,不过,相对于我的期望,它们是不能让我满意的,只能满足我的一小部分解释需要,大致上,他们只能在大的制度框架下解释“小制度”,比如合约安排、交易方式、产权边界和执行机制,等等,但依我看,他们对于“大制度”(比如习惯法、宪政结构、产权起源)和大跨度的经济史,是无能为力的。
举个例子,上述局限其实在张五常身上就表现的很清楚,他把交易费用概念扩大为制度成本,试图以此获得对大制度的解释能力,可是这样一来,新制度经济学反而变成虚谈了,无所不包的交易费用是无法度量的,因为坏的制度所带来的最巨大的“成本”是让大部分技术条件所允许的交易根本没有发生,成本度量就无从谈起,这一点,你看看他对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评论再仔细推敲一下就不难发现,我许多年前在万科论坛上就谈过这个问题,也是从那时候我开始了怀疑。
实际上,看新制度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一项具体制度安排的分析,基本上都需要以存在一个大致上有效的市场为前提,即,存在基本的产权制度和自由交易条件,若没有一组相关市价做参照,成本/收益的度量就不可能,相比之下,博弈论的分析起点条(more...)
最近科学方法论的话题又被提了起来,尽管我时不时会谈论一下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但假如让我做一个全面阐述,或为全面深入学习列举一份适当书单,还是感觉力有不逮,毕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不过,在有所心得时拿出来推荐和讨论一下,我是很乐意的。
我自己在这方面的阅读和清理过程十分困难曲折,花了好多年(中间得到大诗指点,虽三言两语,却受益终生,在此聊记感激),不是典型,大概也不值得模仿。
多数朋友大概不会有兴趣从休谟甚或柏拉图开始到6、70年代的哲学家从头到尾读一遍,但离开某些背景的话我又想不出该如何说明库恩和拉卡托斯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我现在想到一个可能有效率的办法,就是直接去看科学方法论上的长足进展所结出的一些果实,这样可以比较直观的体会其背后的哲学基础的价值所在。
以前称赞过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用一专章(第一卷第一章)交代自己的(more...)
人类女性没有显著的发情期,因而异性难以从其身体外观上判别其排卵时间,这在灵长类里是罕见的,只有我们的近亲倭黑猩猩(bonobo)有类似的情况,而我们另一个近亲黑猩猩(chimpanzee)则有着清晰的发情期。
不过,雌性倭黑猩猩隐藏排卵期的方式与人类恰好相反,她们的外阴有50%的时间处于肿胀状态(这是灵长类雌性发情期的主要识别信号),而发情期清晰的雌黑猩猩肿胀时间只有5%,但她们的排卵频率是一样的,所以,90%的发情信号是虚假广告;相反,女性的做法则是完全不做广告(尽管不能做到彻底的掩盖,据说排卵信号还是会通过面色潮红和气味变化等有所泄露,也有男性声称能加以辨认——有此本领的男同学请举手)。
灵长类学(primatology)家、《黑猩猩政治》的作者Fra(more...)
在有关持枪权的争议中,焦点常常落在枪支的自卫功能上,即便限枪派也会承认,这是值得考虑的需要,然而,拥枪派所提出的另一个理由——维持民间武力以对抗可能出现的暴政,却常常被嗤之以鼻,许多人都认为,以个人轻武器对抗现代军队和国家机器,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轻武器当然无法对抗现代军队,但未必不能在防止暴政上起作用,因为暴政不是一夜间冒出来的,在它发育的过程中,不大会从一开始就动用最强大的工具来对付所面临的挑战,假如在暴政苗头刚刚显露时便遭遇轻武器和松散组织的抵抗,完全有可能被吓的缩回去。
假如你对这一分析不以为然,请看下面这个案例,摘自Jared Diamond的《崩溃》(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第一章(故事发生在蒙大拿州):
在比特鲁谷,激进的右翼保守派人士都是国民自卫队成员,这个组织由当地一些拥有土地(more...)
在比特鲁谷,激进的右翼保守派人士都是国民自卫队成员,这个组织由当地一些拥有土地的人组成,配有武器和弹药,拒绝纳税,禁止别人踏上他们的土地。……这种政治态度的后果之一就是比特鲁谷人反对政府在此进行土地划分或规划,土地所有人认为自己有权对私有财产做任何想做的事。……
1993年,斯蒂夫·鲍威尔在拉法利郡担任委员时,曾召开公共会议,开始讨论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划,并鼓励大众都来思考这一问题,然而,顽固的民间武装组织闯入会场,公然用武器威胁其他居民,斯蒂夫也因此在后来的选举中败北……
前年,在对洪都拉斯宪政危机的评论中,我曾指出,对于支持宪政结构的倒底是哪些东西,或者,某个元素在维持宪政结构中是否有价值,不能仅从它在政治生活的常态中去寻找答案,而更应从那些难得出现的“边界事件”中去观察,许多基础性元素,在平时基础结构未遭遇挑战时,人们常常看不清它们的价值,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似乎连想象它们都是荒谬的,但你不能因此说,它们是没用的。 我想,持枪权的政治意义,大概也属于此类。 我对持枪权的更多评论,参见旧文《美国枪声再起》。拾骨葬,或曰启棺拾骨,貌似在岭南和闽赣客家区都很常见,我在那一带旅行时,常在果林和山腰上见到一排排瓮棺,上面贴着红纸条。
客家行此俗,我猜是跟越人(广义的)学的,因为中原好像无此习俗,而越人中倒是不少见。
这两天在读Alfred Radcliffe-Brown的《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意识到这一葬俗或许有着比百越文化更古老的渊源。
安达曼人(Andamanese)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的后裔,也即俗称的棕色人种(Australoids)中的尼格利陀人(Negrito)人,而在安达曼群岛上,他们长期处于高度隔绝状态(尽管隔绝程度没有塔斯马尼亚人那么高)。
安达曼葬法的前半部分与拾骨葬类似:将死者按特定规制包裹后入土,等皮肉烂净后,将骸骨取出,用水洗净;差别在后面:行拾骨葬者,将骸骨装入瓮棺封好,搬至特定场所(我见过的有果林空地和山腰土龛两种),而安达曼人则将骸骨切割装饰后制作成器物,所以我给种习俗取了个名字叫拾骨作器。
这些器物的功能是巫术性的,放置在居室内或佩戴在身上以祛病辟邪,同时也是种装饰,每件器物最初的佩戴者是(more...)
(按:前天(13日)本博客所在主机出现RAID故障,ISP经多番尝试未能修复,后决定用其最新备份(制作于12日晚)恢复,今日凌晨主机恢复正常。在此期间有许多朋友来电来函亲切慰问,我很感激,并对丢失的评论感到很抱歉,但愿这样的事情不会经常发生。)
最初让我对人类学产生兴趣的,是20年前读到的两本小书:Marvin Harris的《文化的起源》(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s of Cultures)和James Frazer的《魔鬼的律师》(Devil’s Advocate),尽管此前也读过Lewis H. Morgan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但后者完全没有产生绝妙好书所特有的那种当头棒喝眼冒金星的感觉。
不过,如此激起的兴趣,在很长时间里却只是悬吊在那里,被吊起的胃口始终没有找到佳肴来满足它,那时候找本书不容易,而我的钱袋也没鼓到看中本书就能随手买下的程度,所以,我终于“发现”马林诺夫斯基/弗思/布朗/普里查德……并享用一份份大餐,已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
Harris那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猪肉禁忌(pork taboo)和食人俗(cannibalism)的解释,对Aztec的活人殉祭习俗,他的解释简洁而有富有启发:就是为了吃肉,因为Aztec人缺乏蛋白质来源。
Harris的书出版于1975年,正当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和SSSM如日中天之时,当然没什么好下场,Marshall Sahlins带头 标签:
作者从利科尔、弗洛伊德、黑格尔和荣格的著作以及象征人类学著作中吸收了一些观点并加以综合,认为礼仪式食人俗根据人对生命力和死亡的理解,表达了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并运用这种理解来控制那种被认为是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命力。
不好意思,我还真很蛋痛的买了这本书,抄录其中比较搞笑的一段供各位观赏:食人者尚不发达的想象力还不能很恰当地处理隐喻的用法。他被迫完完全全地接纳口部吸吮的欲望。他吃掉某人是由于此人已经以死亡的方式离弃了他。这种缺乏想象力的口部吸吮行为有出于柔情和出于攻击性的方面。像我们所有人一样,食人者也不会察觉此种情形中的攻击性的方面,他发出声音只是出于被卷入这种行为的柔情。
当然,并非所有文化人类学家都像这位资深女文青兼女权主义人类学家那么搞笑的,许多还是相当严肃和现实的,但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他们几乎全都拒斥Harris的“唯物主义”解释,相反,他们都相信食人是一种仪式需要。 问题是,把一种习俗说成仪式并不构成一种“解释”,而仅仅是描述,或用他们喜欢的词汇叫“阐释”,当然,好的功能主义描述能帮助我们看清支撑一个社会结构的那套规范如何组成,如何运作,但也仅此而已,它们并未解释组成规范的各元素何以如此,比如,为何Aztec用人做祭品,而华夏人用牛、Ainu人用熊?纯属偶然吗? 自从看了Harris的解释后,一直没有再看到更多的证据和分析,所以尽管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对食人俗的营养解释也始终将信将疑,但现在,在读完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第9章之后,我的疑虑完全消除了,Harris是对的。 最著名的两个拥有食人俗的社会,墨西哥印第安人和新几内亚山地人,都是缺乏大牲畜的农业社会;我们知道,狩猎采集社会的资源瓶颈常常是卡路里,具体而言就是糖类和脂肪,而农业社会的瓶颈更可能是蛋白质,所以,理想情况下,农耕社会应混合一部分畜牧业,或者能与周边游牧社会建立交换关系,以补充蛋白质来源。 对于欧亚大陆农耕区,尤其是北方农耕区,这个条件能满足,他们的农田附近常有草地或稀树山坡,而他们也驯化了牛羊等大型食草动物,但Aztec人唯一的驯化动物就是狗,所以他们只好把狗当肉畜养,但狗是杂食动物,不吃草,长肉慢,也不产奶,食物产出效率低,结果根本不够吃;相比之下,安第斯印第安农民因为有了羊驼和豚鼠,就既不吃狗和不吃人。 新几内亚山地的条件略好,有猪和鸡,但狗的那些缺点它们同样有:不吃草,长肉慢,不产奶;猪狗鸡的致命缺陷是其食物集与人类的高度重合,与人争食,传统放养条件下,靠主人的食物下脚料喂养,猪狗鸡的生长是很慢的,远不如那些可以放开肚子吃草的牛羊。 食人俗最盛的两个社会恰恰是肉奶最匮乏的两个社会,这显然是对营养解释的极大支持,但仍显不够饱满,不过,当我们考虑过那些处于理想的农业/畜牧混合经济和极度缺乏肉奶的墨西哥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社会之后,营养解释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食狗俗,狗是最早驯化的动物,狩猎采集/游牧/游耕和多数农业社会都不吃狗肉,但华南和东南亚水稻区流行吃狗肉,两个原因:稻米的蛋白质含量低于小麦,水稻区比小麦区更缺乏牛羊而更依赖猪和鸡,这样的推断看来是符合事实的:食狗俗的流行率与水稻种植率正相关,与牛羊缺乏率正相关。 其次是食俗上普遍的南北差异,北方人(包括欧美人)常嘲笑和鄙视南方人什么都吃,除了猫狗,浙江人吃蛤蟆,浙闽都吃老鼠干,广西人吃马肉,广东人更是什么都不放过,但所有这些食俗都与水稻依赖和牛羊缺乏联系在一起,不会都是偶然。 当然,每个社会都会给自己的食俗披上些神话和仪式的外衣,许多古怪的食物都被说成具有滋阴壮阳祛火辟邪的功效,去年我在从化还亲眼目睹了一场用狗血给新买的汽车驱邪的隆重仪式,引擎盖和四个轮子上都被洒上了热气腾腾的狗血。 不错,每个仪式后面都可以说出一大串动听的故事,但需要牢记的是,所有的祭品最后都进了人们的肚子。不知何故,对Jared Diamond那本雄心勃勃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直不抱多大期望,或许是我对畅销书有些偏见吧,但这次显然错了,读过前几章,已让我惊叹:这正是多年来我所期待的那种历史研究啊。
年轻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让我激动过一回,但读过之后留给我更多的却是失望,直到后来Daniel J. Boorstin重新恢复了我对历史学的信心,然后是Fernand Braudel,还有黄宗智,历史学有他们才算上了正轨。
《枪炮》前两部分(即前十章)写的非常好,但从第三部分开始,就明显看得出作者的功力不足之处了,当然,此书主题之设定对功力提出了极高要求,任何作者力有不逮都是可以体谅的,而Diamond宽广过人的知识结构在经济学上显然暴露了缺口。
简单说,Diamond为人类的进化过程能够在欧亚大陆导致如今高度复杂的文明,给出了一个从地理的、生态的、生计模式的、医学的,到制度的、文化的和技术的长链条解释,而在他那(more...)
早先一直觉得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是一种比较“自然”(或者说比较容易想到)的继承制,后来读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时,又觉得蒙古人的幼子继承制(ultimogeniture)其实也蛮有道理,当时没有细想,觉得这事情大概多半是出于偶然吧。
后来又听说诺曼征服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采用幼子继承制,就咯噔了一下,昨天在读Edmund Leach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得知山地克钦(Kachin)人用的也是幼子继承制,忍不住停下来想了想。
琢磨之后,现在我觉得,继承制的选择应该不是偶然的,我目前的结论是:究竟采用长子还是幼子继承制,将取决于:一代人之内创建一份新产业的成功率有多高,该成功率越高,越倾向于幼子继承。
< (more...)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评萨林斯“原初丰裕论”
辉格
2010年12月1日
正在读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 Age Economics),久闻此书大名,刚刚拿到中译本(去年10月出的),读完前两章,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萨林斯的毛病出在哪里了,于是等不及读完就迫不及待要扯上几句。
该书第一章题为“原初丰裕社会”,曾在1968年以论文单独发表(而书出版于1972年),在这一章里,萨林斯对经济学的研究前提提出了质疑;我们知道,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存在价值,它的方法论之所以有意义,都依赖于一个基本假定:资源是稀缺的,这世界上至少有部分资源是稀缺的,否则经济学就没什么好研究了。
对于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家,稀缺性假定有个更强的版本: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生活资料总是稀缺的,换句话说:人口总是被压制在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
然而,基于对狩猎/采集社会和游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萨林斯认为稀缺性根本不是普遍现象,至少在前农业社会不是,他指出,早先许多人类学家受经济学家误导,先入为主的认为狩猎/采集者生产力低下,生活资料匮乏,终日挣扎在生存线附近,遭受贫穷、饥饿、疾病和天灾的困扰。
在萨林斯看来,情况远非如此:狩猎/采集者拥有的东西确实很少,但这并非匮乏,而是他们压根不需要,而他们真正想要的那些东西,并不稀缺,实际上,与农业/工业/商业社会相比,他们的生活算得上很闲适,而人口通常也远低于自然资源所能供养的水平,远离人口压力,萨林斯因此而将这些社会称为“原初丰裕社会”(la première société d’abondance)。
他进而认为,稀缺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现代社会过度膨胀了的欲望所造成,而这种膨胀源于定居、私有产权、等级化、身份差异等等文化因素,并不具有普遍性;他显然意识到,抛弃稀缺性这一前提,经典经济学便无以立足,所以他主张建立人类学(more...)
在How the Mind Works里,Steven Pinker曾介绍了被动物界广泛采用的反阴影保护色(Countershading,也叫Taylor定律),原理是这样的:
动物视觉系统在从背景中识别出物体时,需要某些机制来产生立体感,这些机制包括双眼视差,边缘特征和阴影识别,对于远处的物体,双眼视差很小,阴影就成为更重要的线索;这里的阴影,不仅是指物体在地面上投下的影子,而主要是指物体表面各部分因与光源的相对位置和方向不同而造成的明暗与色差。
Pinker指出,这种识别必须依赖于某些基础假定,比如这里最重要的假定是:光源通常都在物体上方(虽然未必是正上方),所以,在光源照射下,物体的上部总是比下部更明亮,而对于食草动物那种浑圆的躯干,其明暗过度有着特定的分布。
所以,当一种动物不想被其他动物看到时,就需要发明一些机制来阻止上述识别机制的正常工作,办法之一是用斑点/条纹来扰乱特定的明暗分布,但更普遍的办法,是反阴影:在躯干下方长出颜色更浅的皮肤或毛发。
于是我们看到,大部分四足行走的动物,腹部的颜色总是比背部的浅,而在鱼类,我们看到的就是鱼肚白;相反,那些生活在树冠上的灵长类,腹背色差就没那么明确。
可是肚白方案在某些情况下会失效:假如你生活在较深的海水里,而你的主要天敌通常从更深处的正下方向上发动攻击,此时,无论你的肚子有多白,你的身体总是挡住了从水面上方进入的光线。
这种时候,你所需要的实际上是一件隐身斗篷,你唯一能欺骗捕食者的方法,似乎就是让光线绕过你的身体继续前进,当然,做到这一点太难了,不过还有一个相对容易的办法:在你肚子里装个灯泡,发出看上去和来自水面上的近似的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