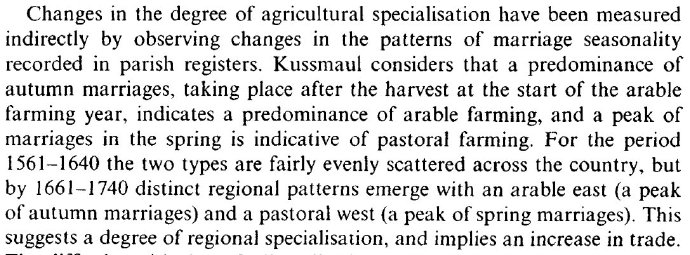含有〈历史〉标签的文章(169)
辉格
@ 2021-08-25 10:09
阅读(1,371)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1-08-25】
Razib Khan 又一篇好文章,讲的是匈牙利人的奇特历史,
匈牙利语属于乌拉尔语系乌戈尔语族,该语族的另外两个群体是汉特人和曼西人,远在匈牙利平原几千公里之外的西伯利亚,

可奇怪的是,当今匈牙利人在遗传特征标记上和他们的西伯利亚表亲毫无关系,而和他们目前的东欧邻居几乎看不出区别,
一个群体怎么会在保持其语言的同时丢失了全部遗传特征?
最近十几年古DNA测序技术发展神速,所以有人就从10世纪的马扎尔人墓葬中提取了DNA,发现其中上层精英的DNA确实有显著的东亚成分,而同地(more...)
标签:人类 | 历史 | 族群 | 语言 | 遗传
8780
【2021-08-25】
Razib Khan
又一篇好文章,讲的是匈牙利人的奇特历史,
匈牙利语属于乌拉尔语系乌戈尔语族,该语族的另外两个群体是汉特人和曼西人,远在匈牙利平原几千公里之外的西伯利亚,

可奇怪的是,当今匈牙利人在遗传特征标记上和他们的西伯利亚表亲毫无关系,而和他们目前的东欧邻居几乎看不出区别,
一个群体怎么会在保持其语言的同时丢失了全部遗传特征?
最近十几年古DNA测序技术发展神速,所以有人就从10世纪的马扎尔人墓葬中提取了DNA,发现其中上层精英的DNA确实有显著的东亚成分,而同地区的平民遗骸则没有,
所以当初侵入匈牙利平原的马扎尔人确实来自东方,问题是他们的遗传特征跑哪儿去了?
一种解释是当初的征服者群体规模非常小,所以东方成分被稀释了,统计上看不出差异,
问题是,历史上许多案例证明,小规模征服群体很难保持其母语,特别是没有教育传统也没有成文经典的蛮族,比如侵入伊比利亚和北非的汪达尔人,语言上一丝痕迹也没留下,
所以,保留了其母语的马扎尔人当初必定是个大群体,而且女性比例得足够高,如果娶的都是当地女子,母语难免丢失,因为在没有教育系统的情况下,婴儿主要跟母亲学母语,
Razib Khan 认为,这可能因为,自从马扎尔贵族皈依基督教后,匈牙利成了基督教世界的东方门户,而匈牙利平原又是东方入侵者的天然指向(因为它是欧亚草原带的西端),所以长期承受着军事上的重压,特别是在蒙古和奥斯曼的入侵中,其贵族阶层屡次被大比例消灭,最终从遗传统计上消失,
一般而论,武士贵族是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态位,通常相对于平民都有着较大遗传优势,但也有不幸赌输了的,马扎尔贵族算是一例,
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所谓魏晋风度,玄学清谈之风,其实都是九品中正制给刺激出来的,
汉代取士选官的方法是察举制,由郡守选拔有才者推荐给朝廷,但郡守都是单车赴任的外地人,所知有限,所以候选名单还是要靠地方乡老的评议和举荐,而有机会在这种事情上发表意见的,自然都是当地上层人物,
随着官僚体系的确立,这条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诱人值钱,也越来越拥挤,于是,地方上那些有势力高地位的豪族,便开始设法垄断这条通道,将郡守的选择范围限制在他们这个地位既已确立的小圈子里,
但这一垄断并未完全成功,不少人利用与上层的直接关系(比如与外戚和宦官的关系)绕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称为浊流,而从豪族门第系统入仕的则是清流,
所以有关谁有资格走进这条通道的争议和冲突始终存在,而且随着通道变拥挤而日益(more...)
标签:历史 | 地位 | 声望 | 官僚 | 文化
8728
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所谓魏晋风度,玄学清谈之风,其实都是九品中正制给刺激出来的,
汉代取士选官的方法是察举制,由郡守选拔有才者推荐给朝廷,但郡守都是单车赴任的外地人,所知有限,所以候选名单还是要靠地方乡老的评议和举荐,而有机会在这种事情上发表意见的,自然都是当地上层人物,
随着官僚体系的确立,这条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诱人值钱,也越来越拥挤,于是,地方上那些有势力高地位的豪族,便开始设法垄断这条通道,将郡守的选择范围限制在他们这个地位既已确立的小圈子里,
但这一垄断并未完全成功,不少人利用与上层的直接关系(比如与外戚和宦官的关系)绕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称为浊流,而从豪族门第系统入仕的则是清流,
所以有关谁有资格走进这条通道的争议和冲突始终存在,而且随着通道变拥挤而日益加剧,最后终于在汉末爆发为党锢之祸,
九品中正制的意图,正是为了平息此类冲突,将察举制规范化,减少整个筛选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办法是,将确定入仕优先次序的决定完全交给地方豪族之间的评议机制,豪族们对其子弟的相互评价结果将决定一位入仕候选者的乡品(1-5品),而乡品将决定他开始做官时的起家官品(1-9品),算法是:起家官品=乡品+4,(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篇第2章)
而朝廷派往地方的中正,其实只是确认这个评议和排序结果,
这一改变显然强化了豪族的垄断权(这一垄断最终造就了士族门阀),束缚了地方官和朝廷的选择范围,将竞争的焦点前移到了乡议环节,结果就是,随乡议而展开的声望竞赛白热化了,而清谈玄学正是声望竞赛的一部分,
竹林七贤看似淡泊名利,放浪形骸,其实个个都做上了官,
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品评人物,组成了乡议主要部分,
清谈的另一个目的是智力和品味竞赛,为何它们的内容会变得那么玄奥和清奇?因为任何此类竞争在白热化之后都会走进一些特别狭窄离奇的偏门左道,非如此无法凸显你的特别之处,正如我们在先锋艺术和实验电影里常看到的那样,
魏晋名士不仅爱豪饮,裸奔,还爱嗑药(五石散),这些出格离奇之举,依我看,背后都有着明确的功利动机——提高自己的乡品,
这跟当代 woke 们那些荒谬言论背后的动机一样,难道真有那么多人会相信两性差异完全没有生物学基础?
这里又可以看到我早先说过的
安全距离原理在起作用,假如你已经非常安全的确立了*你是个聪明人*的地位,那么,你说一句听起来好像很愚蠢的话,并不会因此而被视为蠢人,反而还可能让听者疑惑:这句话里是不是有什么我未能理解的深意?因而不敢质疑你,甚至积极附和你,而这一附和进而也影响了更多听众的反应——既然这些聪明人都在附和他,这句话里肯定有什么我没能理解的深意,所以,为了不暴露我的愚蠢,最好也跟着附和,于是,皇帝新衣就这么穿起来了,
可是,假如你的聪明人地位并不牢靠,你就不敢玩这种游戏,
【2021-07-14】
我发现Ken Follett在中国好像也很热门,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有中译本,去年9月的新作今年3月就有了中译本,很少见的待遇,
我没读过他的书,不过我看过根据他小说 World Without End 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对中世纪的理解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当然,很多人喜欢他可能只是基于作品的文学价值,这个我没读过没资格评论,我只是想友情提醒一句,你要是靠他的作品来理解中世纪英格兰社会的话,那会错的很离谱,
(more...)
8712
【2021-07-14】
我发现[[Ken Follett]]在中国好像也很热门,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有中译本,去年9月的新作今年3月就有了中译本,很少见的待遇,
我没读过他的书,不过我看过根据他小说 World Without End 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对中世纪的理解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当然,很多人喜欢他可能只是基于作品的文学价值,这个我没读过没资格评论,我只是想友情提醒一句,你要是靠他的作品来理解中世纪英格兰社会的话,那会错的很离谱,
我觉得值得这么提醒一下,是因为从改编的电视剧看,他作品的细部描绘看起来特别写实和质感,所以尤其具有欺骗性,让你感觉好像很真实的样子,
辉格
@ 2021-07-05 21:16
阅读(1,319)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1-07-05】
古代温带地区的战争多数是在春夏两季发动的,若是打到仲秋还未决出胜负,多半也只能收场,打不下去了,
导致这种季节性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比较容易想到,如果士兵大多是农民,春耕秋收期间打仗损失就很大,士气也大受影响,
另一个原因不太受关注,在火车轮船之前,陆上的补给运输主要靠牛马,假如这些牛马沿路无草可吃,它们就要用掉很大一部分载荷来运输饲料,这一比例取决于两个补给点之间的距离,当距离大到某个极限时,有效载荷降至零,牲口再多也没用了,
(more...)
8693
【2021-07-05】
古代温带地区的战争多数是在春夏两季发动的,若是打到仲秋还未决出胜负,多半也只能收场,打不下去了,
导致这种季节性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比较容易想到,如果士兵大多是农民,春耕秋收期间打仗损失就很大,士气也大受影响,
另一个原因不太受关注,在火车轮船之前,陆上的补给运输主要靠牛马,假如这些牛马沿路无草可吃,它们就要用掉很大一部分载荷来运输饲料,这一比例取决于两个补给点之间的距离,当距离大到某个极限时,有效载荷降至零,牲口再多也没用了,
这个运输瓶颈意味着,哪怕军队全部由无须务农的职业士兵组成,战争的季节性仍无可避免,
沿路若是有一些河道或海港可用,瓶颈会得到缓解,而越是深入内陆且远离通航河道的地方,这个问题越突出,
当然,这里说的是至少几千几万人的大仗,几十数百人的袭扰和劫掠则另当别论,
辉格
@ 2021-05-16 18:02
阅读(1,976)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1-05-11】
@whigzhou: 客家人就是中国的边民,在许多方面都跟英国的 Scotch-Irish 很像:占据的是贫瘠的边缘生态位,民间秩序发达,反官方,好斗,出战士,一有仗打出头机会就来了,太平天国和国共之争就不说了,在东南亚的表现就很鲜明,南洋华人经商挣钱都没问题,可是一起风波就全是砧上鱼肉,唯有客家人是例外,楞打出了个兰芳共和国,
@whigzhou: 客家人的崛起其实源自于玉米土豆的引入,他们凭借这些旱地作物向山区大规模扩张,挤占了原本由畲瑶占据的生态位,将后者消灭或同化,同时在新生态位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并实现规模扩张
@wwwwww_wwwwwww:好奇这么能打为什么没有占领平原地区的田地,还是很多待在山区呢?
@whigzhou: 这恰好说明,个体或小团伙的战斗力并不足以让他们对抗国家机器,若要冒头,他们要么为机器效力,要么机器本身崩坏,要么冒出一位组织(more...)
标签:历史 | 客家 | 文化 | 民族 | 移民 | 边民
8613
【2021-05-11】
@whigzhou: 客家人就是中国的边民,在许多方面都跟英国的 Scotch-Irish 很像:占据的是贫瘠的边缘生态位,民间秩序发达,反官方,好斗,出战士,一有仗打出头机会就来了,太平天国和国共之争就不说了,在东南亚的表现就很鲜明,南洋华人经商挣钱都没问题,可是一起风波就全是砧上鱼肉,唯有客家人是例外,楞打出了个兰芳共和国,
@whigzhou: 客家人的崛起其实源自于玉米土豆的引入,他们凭借这些旱地作物向山区大规模扩张,挤占了原本由畲瑶占据的生态位,将后者消灭或同化,同时在新生态位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并实现规模扩张
@wwwwww_wwwwwww:好奇这么能打为什么没有占领平原地区的田地,还是很多待在山区呢?
@whigzhou: 这恰好说明,个体或小团伙的战斗力并不足以让他们对抗国家机器,若要冒头,他们要么为机器效力,要么机器本身崩坏,要么冒出一位组织天才
@whigzhou: 游牧者同理
@季路一言围脖:哥萨克也同理吗?
@whigzhou: 是
@鲁大郎:国共之争?求解释
@whigzhou: 孙文的兴中会几乎清一色客家人,同盟会也是客家为主力,黄花岗72士一半客家,民国境内曾有过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中华共和国,两者皆以客家区为基本盘
【2021-05-16】
@渔父_:李辉的《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说:“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类苗瑶结构来自湖北和广东”;“客家话是南方原住民语言在中原汉语不断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大伯觉得这种猜想靠谱吗?
@whigzhou: 同意第一句
@whigzhou: 其实不只是客家,整个南方汉族都有相当高的旧土著成分,南方的旧土著大致分侗傣和苗瑶两系,侗傣倾向于占据平原河谷低地生态位,苗瑶(包括畲族)倾向于高地,所以客家吸纳苗瑶成分更多,当在情理之中,
不过『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1)区分哪个是核心好像没什么意义,2)把这些旧土著称为荆蛮族是过强的判断,是对古代含糊概念的不恰当复活,3)加入的汉族成分不仅是中原移民,久已定居当地的汉人也会因人口压力而持续向高地渗透,
『类苗瑶结构来自湖北和广东』我看没什么根据,苗瑶在整个南方都有分布,
『客家话是南方原住民语言在中原汉语不断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客家话的主干恐怕还是汉语,依我看,其苗瑶成分是汉语主干吸纳进去的,而不是苗瑶语内核裹上了汉语成分,当然,我不打算为这种区分赋予某种本质主义意味,
@whigzhou: 强势群体扩张吸纳当地土著群体的过程中,普遍规律是,吸纳的女系成分会远远高于男系成分,这一点在南方汉族中应该不会例外,虽然我还没看过数据,
@辣目海伦:北方汉人南下时都是落魄的,不是战争被赶过来避难就是被罚来南边,哪来优越感?
@whigzhou: 且不论是否都是『被赶过来避难』的,就算是,也照样可以优越,扫荡罗马的匈人,称雄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都是被其他游牧者从东边赶过来避难的
@whigzhou: 永嘉南渡的士族,唐末南迁的汉人,都是颇具规模的武装组织,虽然大秩序瓦解,但这些局部组织对付南方的土著群体还是绰绰有余
@离群索居bj:从东边赶过去的都挺勇猛啊,是不是说明赶他们过去的东方人比西方人要厉害呢?至少在武力上
@whigzhou: 不可作此推论,至少在个体和小团伙层次上不可,游牧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兴衰勃忽无常,一旦组织起来了,就很厉害,平时散沙状态,也就小打小闹,或给人当雇佣兵,所以,被赶走的,未必是弱者
@whigzhou: 青铜时代伊朗语族游牧者从西往东是大趋势,秦汉之后阿尔泰语系游牧者从东往西是大趋势,理由在组织层面而非个体/团伙战斗力差异
@日日用功有常:《世界简史》认为游牧者从东向西的潮流的根源是南俄草原,或者说亚欧大草原西端水草丰美。
@whigzhou: 这解释完全站不住,果若如此,1)匈人到了南俄就该歇了,怎么还继续往西,2)阿兰人本来就在南俄,为啥往外跑,3)若西迁动力是吸而非推,那么匈人应该比突厥先动,事实相反
@whigzhou: 这种说法和诸如*温州徽州人擅经商是被山区人多地少给逼的*之类是同样的无稽之谈,既没有经验证据,也经不起理论推敲
@kingsmill:哈哈哈按同类逻辑甘肃人也应该善于经商[允悲]
@whigzhou: 说这种话的人脑子里没有一点点均衡的概念(或者用经济学黑话叫无差异原则),山地土地贫瘠,承载能力低,人口自然稀疏,平原谷底承载能力高,人口密度就上去了,若其他条件相同,边际上无差别
@whigzhou: 以华南的经验,肥沃河谷三角洲的人均耕地低至1-2亩,山地则十几甚至几十亩,资本/技能相当时,边际上无差异,也就是往外寻出路的动力是一样的,表现特异者必定有其他缘故
@公馆森田忍1_O::我们家就是粤东的客家人,家族里有本流传下的族谱,里面记载的先祖是商王朝时期人,祖地在今河南南阳
@whigzhou: 除非有其他史料佐证,家谱上提到的任何早于南宋的东西都默认视为美丽传说
【2021-05-09】
和澳洲相比,西伯利亚流放系统在推动殖民上的效果很差,流犯逃亡比例极高,很少定居下来,而作为劳动力,他们也不受当地农民欢迎(相比之下,澳洲农场主对流犯劳力的需求非常旺盛),更糟糕的是,当局对流犯的约束、影响和引导能力很弱,结果西伯利亚简直成了个大型练蛊盆(练出的最大两只蛊就是俄罗斯黑手党和布尔什维克),
想了想,造成这个差异的各因素中,有几点好像比较突出:
1)西伯利亚其实没有那么孤绝,至少孤绝程度跟澳洲比差远了,而且流犯很清楚该从哪条路线、向哪里逃——只要沿着被送过来的那条路朝相反方向走即(more...)
8607
【2021-05-09】
和澳洲相比,西伯利亚流放系统在推动殖民上的效果很差,流犯逃亡比例极高,很少定居下来,而作为劳动力,他们也不受当地农民欢迎(相比之下,澳洲农场主对流犯劳力的需求非常旺盛),更糟糕的是,当局对流犯的约束、影响和引导能力很弱,结果西伯利亚简直成了个大型练蛊盆(练出的最大两只蛊就是俄罗斯黑手党和布尔什维克),
想了想,造成这个差异的各因素中,有几点好像比较突出:
1)西伯利亚其实没有那么孤绝,至少孤绝程度跟澳洲比差远了,而且流犯很清楚该从哪条路线、向哪里逃——只要沿着被送过来的那条路朝相反方向走即可,沿路虽人口稀疏,但还是有足够多的村庄可供乞讨勒索抢劫以获取给养,结果是,流犯逃亡率超过1/3,而且成功率也不算低,大概有一小半能逃回乌拉尔以西,
因为逃亡者足够多,沿路很容易几十个人凑成一伙,就更提高了给养获取能力和逃亡成功率,所以,任何时候西伯利亚道路沿线都有一群群的逃亡者在从东往西跑,被戏称为西伯利亚永动机,
由于不受当地农民欢迎,他们在农业拓殖没多少贡献,对殖民事业的作用仅限于在各种公共工程上做苦力,但那其实也是很没效率的,远不如直接花钱雇人合算,
2)发配西伯利亚的政治犯很多,越到后期越多,这些镇痔犯很多是贵族,或至少中上层知识分子,家里有钱,每年几千几万卢布往那儿寄,这么多钱花下去,足以把整个看守团队变成他们的仆人,加上制度上的贵族特权待遇,这些人在流放地的活动相当自由,阅读、写作和通信毫无障碍(除了几个月的延迟之外),甚至还能办报刊,总之,官方很少能影响这群人的活动,反倒他们对流犯群体和当地社会影响很大,
3)发配西伯利亚的重罪犯很多,包括谋杀抢劫者,这些人很难管束,加上俄国官僚机器的腐败低效,结果流犯群体就像黑社会那样发展出了自己的秩序和组织体系,官方对其走向的引导控制能力很差,
暴力重犯多可能也是他们不受农民欢迎的原因之一,
那么为何俄国流犯的重犯比例比澳洲高呢?依我看,是因为俄国很少用死刑,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废除死刑,后来虽然恢复,但很少用,像杀人抢劫这种重罪犯,在英国可能就吊死了,不会送去澳洲,送去的多数是偷窃伪造之类,
俄国死刑少到什么程度,有个例子可以说明,1846年一群四个逃犯把一整个金矿勘探队十几号人杀了个精光,结果居然没人因此判死刑,只是夹道鞭笞和终身苦役,
辉格
@ 2021-04-13 21:20
阅读(1,528)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1-04-13】
之前读了 Robert Hughes《致命的海滩》,把澳洲流放史讲的非常细,流放制度比我原先认为的要复杂,是个层次丰厚而且十分动态的系统,
流放时代,澳洲居民按社会地位高低大致分这样几类:
1)组成殖民地治理团队的军官,
2)自由移居者,
3)刑满释放的前流犯,
4)刑期未满的流犯,
刑期分7年,14年,终身(极少数)三档,不过在释放之前,刑期始终可能随表现而增减,
最有意思的是,服刑流犯的状态本身就非常多样,随自由度高低不同而构成一部层次丰富的阶梯,大致有这么几级:
1)最自由的,是拿到了假释证的那些,他们除了不能离开澳洲之外,和自由人无异,
2)其次是配(more...)
8543
【2021-04-13】
之前读了 Robert Hughes《致命的海滩》,把澳洲流放史讲的非常细,流放制度比我原先认为的要复杂,是个层次丰厚而且十分动态的系统,
流放时代,澳洲居民按社会地位高低大致分这样几类:
1)组成殖民地治理团队的军官,
2)自由移居者,
3)刑满释放的前流犯,
4)刑期未满的流犯,
刑期分7年,14年,终身(极少数)三档,不过在释放之前,刑期始终可能随表现而增减,
最有意思的是,服刑流犯的状态本身就非常多样,随自由度高低不同而构成一部层次丰富的阶梯,大致有这么几级:
1)最自由的,是拿到了假释证的那些,他们除了不能离开澳洲之外,和自由人无异,
2)其次是配给劳工,就是由当局分配给某位农场主,给他做工,状况类似于契约劳工,对于早期自由移民,有机会获得配给劳工是一个主要的吸引点,因为自由雇工几乎找不到,找到也价格极高,因为自由移民很容易从当局获得几百几千英亩的赠地,不会甘愿替人打工,
不过在最初,获得配给劳工的农场主不一定是自由移民,因为在处女地开拓农场非常困难,任何人只要能这能力,都会得到机会,包括流犯,而流犯里面会种地的人极少,
3)然后是那些在殖民当局直接控制下干活的人,其中比较自由的是那些有特殊技能的人,比如石匠木匠造船匠,还有能读会写的,后者主要来自伪造文件者,这些人会被当局挑出来,放到与其技能相配的岗位上,处境比配给劳工更好,
4)这一级是新到达流犯的默认起点,他们在当局工头(通常是一位低级军官)的监督下为公共工程干活,主要是盖房修路,所以也叫公路帮,
5)前面几级中,表现不好的,会被发配到铁链帮,他们的工作内容和(4)差不多,但是处于更严格的监禁条件下,通常白天干活时带着脚链,晚上会被关在牢房里,而且为防止逃跑,往往会选择一个极为孤立蛮荒的新拓居点,
6)流犯中最冥顽不化的那些,比如反复逃跑者,会被发配到离大陆一千多公里的诺福克岛,那里被刻意安排成生不如死的人间地狱,也叫垃圾场的垃圾场,常会把暴虐出名的军官派去负责,
这样一部层次丰厚的阶梯,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流犯好好表现,养成劳动习惯,然后顺着阶梯往上爬,尽快重获自由身,
不过,实际执行中,这种激励效果是否充分体现,取决于执行者是否公正,所以各地各时也参差不齐,执行最到位的是 George Arthur 治理下的塔斯马尼亚,他给每位流犯建立了完整档案,并采用一种非常细致的打分系统,打满多少分就自动往上升,反之往下掉,
与个体流犯在其上升降的阶梯相映成趣的,是各拓殖点也依次构成了一条渐变光谱,
每个拓殖点一旦开拓成功(表现为农业取得收益),基础设施建立,就会吸引更多自由移民,刑满或假释流犯也会定居下来,老移民会生下孩子,于是自由民就提高了,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不想再看到一群群带着脚镣的流犯四处晃荡,认为这有损于社区的形象、声誉和治安,于是当局便面临压力寻找新的拓殖点,
况且,即便没有自由民的压力,当局自己也有这需要,因为当拓殖点变得更像一个正常成熟社会之后,对流犯就没那么可怕了,也容易逃脱了(不像在孤绝蛮荒之地,逃出去基本上也是死),
所以,为了安置上面(4)(5)两级的流犯,当局必须不断寻找新的拓殖点,并且由若干新旧拓殖点构成一个从最成熟到最蛮荒最艰苦的光谱,提供不同的惩罚强度,用来安置不同级别的流犯(在此意义上,第5级其实可以随地点不同而细分成多级),
这一为满足流放功能需要而开拓的历史,贯穿着澳洲的早期殖民史,从悉尼开始,霍巴特,亚瑟港,菲利普港(不久后放弃),纽卡斯尔,麦夸里港,布里斯班,最后是Fremantle(当今Perth的一部分),这个拓殖进程,也对应着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昆士兰和西澳的建立,只有维多利亚和南澳的历史不在这条主线上,维多利亚基本上是由自由移民建立的(又因淘金热而壮大),而南澳最初是由渔民和捕鲸者所开拓
辉格
@ 2021-04-10 16:08
阅读(1,571)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1-04-10】
菲利普和伊丽莎白这段姻缘,有个重要背景,就是一战造成的欧洲王族圈大撕裂,一战前,欧洲各国打来打去,但并不影响王室间持续通婚,一战中,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彻底压倒上层的传统婚姻纽带,迫使各王族成员不得不站队表态,
英国王室自汉诺威朝以来就有很深的德意志渊源,为了表态只好将族姓从萨克森-科堡-哥塔改为温莎,
菲利普的爷爷乔治当初被挑出来做希腊国王,是因为当时丹麦足够弱小,由他接位可以避免吞并之嫌,符合1832年《伦敦协议》不许任何强国王族获取希腊王位的原则,而且乔治的两个姐姐分(more...)
8539
【2021-04-10】
菲利普和伊丽莎白这段姻缘,有个重要背景,就是一战造成的欧洲王族圈大撕裂,一战前,欧洲各国打来打去,但并不影响王室间持续通婚,一战中,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彻底压倒上层的传统婚姻纽带,迫使各王族成员不得不站队表态,
英国王室自汉诺威朝以来就有很深的德意志渊源,为了表态只好将族姓从萨克森-科堡-哥塔改为温莎,
菲利普的爷爷乔治当初被挑出来做希腊国王,是因为当时丹麦足够弱小,由他接位可以避免吞并之嫌,符合1832年《伦敦协议》不许任何强国王族获取希腊王位的原则,而且乔治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爱德华七世和亚历山大三世,很适合平衡需要,
一战中,希腊王族也被迫站队,当时希腊民众强烈亲英(实际上他们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就一直亲英,当时选定乔治之前,希腊民众在公投中95%投给了维多利亚的儿子阿尔伯特),可是乔治的继任者君士坦丁是个亲德分子,但也不敢公开得罪英国,所以选择中立,结果希腊两派就打翻了,
这次站队错误给了希腊沉重打击,在紧接着一战的希土战争中,希腊既没得到英国的实质性支持,也没在国内建立团结一致的力量,惨败之后,王室遭驱逐,菲利普一家便在其中,
可是撕裂并未结束,随着英德关系再次紧张,欧洲王族很快面临另一轮站队,菲利普的四个姐姐全部站到了德方,嫁给了德国贵族,只有菲利普跟着他母亲站到了英国一方,
而他母亲的立场正是上一轮站队的结果,他外公路易是黑森的公子,因为继位无望而跑到英国,加入皇家海军,并且一路腾达,一直做到第一海军大臣,一战期间,也是为了断绝德意志渊源,把族姓从巴登堡改成了蒙巴顿,他儿子路易·蒙巴顿,就是后来的印度末代总督,战后也曾出任第一海军大臣,和帝国参谋总长,
就是在二战前的风云时刻,菲利普步外公和舅舅的后尘,加入了皇家海军,并且采用了蒙巴顿这个娘家姓氏,
就在同一年,乔治六世夫妇前往皇家海军学院巡视,菲利普的舅舅路易·蒙巴顿(当时也在海军服役,而且是宫廷红人)承机让正好在海军学院受训的菲利普陪同公主,这才有了13岁纯情少女向18岁大表哥求爱的千古佳话
辉格
@ 2021-04-03 09:54
阅读(1,458)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1-04-03】
比利时有个小城叫Baarle-Hertog,总共7.48平方公里,2700人,不仅整个处于荷兰境内,而且碎作24块,镇上人随便散个步就出国回国好几趟,喝酒喝到一半,去上个厕所,又出了两次

@何不笑:有意思。不知这个局面是怎么形成的。某个时刻按民族/语言/传统啥的自决?
@whigzhou: 几位领主之间土地零星转让的结果,德国统一之前西北部那些小邦的领土也都非常碎,也是长期零星交易积累下来的结果,只是碎片程度没这么极端
 标签:历史 | 土地 | 地理
标签:历史 | 土地 | 地理
8523
【2021-04-03】
比利时有个小城叫Baarle-Hertog,总共7.48平方公里,2700人,不仅整个处于荷兰境内,而且碎作24块,镇上人随便散个步就出国回国好几趟,喝酒喝到一半,去上个厕所,又出了两次

@何不笑:有意思。不知这个局面是怎么形成的。某个时刻按民族/语言/传统啥的自决?
@whigzhou: 几位领主之间土地零星转让的结果,德国统一之前西北部那些小邦的领土也都非常碎,也是长期零星交易积累下来的结果,只是碎片程度没这么极端

@whigzhou: 再比如列支敦士登,现在领土只有160平方公里,以前在捷克和波兰有很多领地和城堡,总面积比老巢大十几倍,二战后都被没收了
辉格
@ 2021-03-29 17:55
阅读(1,508)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1-03-29】
塔斯马尼亚(当时还叫 Van Diemen’s Land )副总督 George Arthur 在1830年向当地土著发出的告示,画在木板上,制作了很多份,悬挂于各地,是殖民者与无文字土著沟通的一个有趣案例

@蘸盐: 然而塔斯马尼亚人最后还是被澳大利亚白人给杀光了。连20世纪的希特勒都没实现的、对一个种族的彻底的灭绝,19世纪的澳大利亚人做到了[思考]武装白人组成阵列线横扫全岛,搜山括海捕猎塔斯马尼亚人,总督还设立了名为“Black catching”的奖金,
@whigzhou: 将白人视为同质群体,得到的就是这种叙事(more...)
标签:伦理 | 历史 | 文字 | 殖民 | 澳洲 | 语言
8511
【2021-03-29】
塔斯马尼亚(当时还叫 Van Diemen's Land )副总督 George Arthur 在1830年向当地土著发出的告示,画在木板上,制作了很多份,悬挂于各地,是殖民者与无文字土著沟通的一个有趣案例

@蘸盐: 然而塔斯马尼亚人最后还是被澳大利亚白人给杀光了。连20世纪的希特勒都没实现的、对一个种族的彻底的灭绝,19世纪的澳大利亚人做到了[思考]武装白人组成阵列线横扫全岛,搜山括海捕猎塔斯马尼亚人,总督还设立了名为“Black catching”的奖金,
@whigzhou: 将白人视为同质群体,得到的就是这种叙事
@whigzhou: 杀土著的主要是逃亡流犯,他们逃到野外只能靠打袋鼠生存,与土著形成同生态位竞争,其次是拓殖前线的农场主,与土著频繁冲突,而殖民当局花了很大力气遏制这些冲突,避免土著被消灭
@whigzhou: 塔斯马尼亚适合拓殖的其实只有南北走向的那条中央谷地,面积不到全岛的1/3,剩下的2/3本来足够人口只有几千的土著过日子,而且当局也有意将这2/3留作他们的保留地,问题是这事情没法落实,因为塔斯马尼亚土著(和整个澳洲的土著一样,而不像北美土著)没有比游团更大的社会结构,你既找不到人谈判,也没有政治领袖能约束土著行为,当局也曾试图将土著从中央谷地驱赶到拟议中的保留地,但很难有成效,因为牧场对土著的吸引力太大,这也不难理解,毕竟抓羊比打袋鼠容易多了,而且羊肉也比袋鼠肉肥的多,
塔斯马尼亚土著的灭绝是不是当局政策的后果,对比一下新西兰毛利人的情况就容易理解,毛利人(和其他波利尼西亚人一样)是有复杂社会结构的,时而还能建立起酋邦这样的大型政体,所以毛利人的土地权得到了相当完整的认可,拓殖者都是通过正式条约和买卖契约来获得土地的,毛利人和殖民者的关系相当不错,一战二战时都主动要求组建毛利军团参战
@蒋培锋:难道不是因为有一定的武力吗?
@whigzhou: 1)欧洲殖民者中有没有罪恶或不义行为?
当然有,而且不少,
2)那么,基于何种伦理标准,说这些行为是不义的?
基于过去几百年中逐渐确立并取得主流地位的西方伦理,特别是盎格鲁伦理,
在这套价值观未被接受的社会,灭个异族根本不算事儿,
3)所以,当你大声谴责(1)中那些不义之举时,最好先想想清楚,你是不是准备大力弘扬西方价值观?
如果你回答*是*,那我们倒可以讨论一下这些不义究竟有多普遍多严重
辉格
@ 2021-03-14 20:43
阅读(1,548)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1-03-14】
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威斯康辛,伊利诺伊,密苏里,这些州有个共同点:它们的最大城市都紧贴着其东部边界,这并非巧合,都体现了西进运动中开拓者的前瞻性,
另外,堪萨斯和明尼苏达也勉强可以归入其中,堪萨斯城的堪萨斯部分若是单算,也是堪萨斯州的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离明尼苏达的东部边界有点距离,但也不远,目前已经贴上了
8484
【2021-03-14】
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威斯康辛,伊利诺伊,密苏里,这些州有个共同点:它们的最大城市都紧贴着其东部边界,这并非巧合,都体现了西进运动中开拓者的前瞻性,
另外,堪萨斯和明尼苏达也勉强可以归入其中,堪萨斯城的堪萨斯部分若是单算,也是堪萨斯州的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离明尼苏达的东部边界有点距离,但也不远,目前已经贴上了
【2021-02-04】
13世纪西多会修道士(Cistercians)设计的数字符号系统,用字符的四个象限分别表示一个十进制位,因而每个字符可表示1-9999之间的任何数值,非常紧凑的设计方案,图中最后一行是几个应用示例

@R档狂飙2021:看似精妙但使用起来较阿拉伯数字有何优势呢。
@whigzhou: 比(其替代对象)罗马数字有优势就行了
@殆知喵:仓廪实然后好玩耍[可爱]//@重生字幕组:修道院里吃饱撑着的[允悲(more...)
8425
【2021-02-04】
13世纪西多会修道士(Cistercians)设计的数字符号系统,用字符的四个象限分别表示一个十进制位,因而每个字符可表示1-9999之间的任何数值,非常紧凑的设计方案,图中最后一行是几个应用示例

@R档狂飙2021:看似精妙但使用起来较阿拉伯数字有何优势呢。
@whigzhou: 比(其替代对象)罗马数字有优势就行了
@殆知喵:仓廪实然后好玩耍[可爱]//@重生字幕组:修道院里吃饱撑着的[允悲][允悲][二哈]
@whigzhou: 修士可不是闲人,修道院是中古欧洲规模化企业的先驱,农工商经营都很活跃,许多产业都是他们开创的,许多技术创新(比如水动力系统)也来自那里,这也是为何他们无法忍受罗马数字系统
辉格
@ 2021-01-23 11:52
阅读(2,249)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1-01-23】
历史学家为了从有限史料中榨出一点点信息真是绞尽脑汁,前现代英格兰保存最完整的史料是洗礼、婚姻和遗嘱记录,所以各路史家都拼命从中淘数据,Kussmaul 注意到,以谷物耕种为主的地区,结婚高峰在收获后的八月,而以畜牧为主的地区,结婚高峰在春季产仔高峰之后,基于这一特征,他发现,17世纪英格兰农业的地区专业化程度明显高于16世纪,非常聪明的方法(引文摘自: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p.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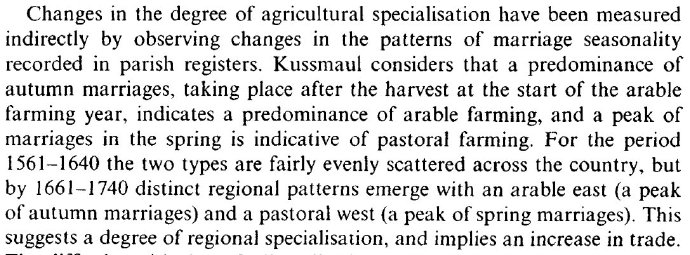 标签:农业 | 历史 | 婚姻 | 方法 | 科学
标签:农业 | 历史 | 婚姻 | 方法 | 科学
8407
【2021-01-23】
历史学家为了从有限史料中榨出一点点信息真是绞尽脑汁,前现代英格兰保存最完整的史料是洗礼、婚姻和遗嘱记录,所以各路史家都拼命从中淘数据,Kussmaul 注意到,以谷物耕种为主的地区,结婚高峰在收获后的八月,而以畜牧为主的地区,结婚高峰在春季产仔高峰之后,基于这一特征,他发现,17世纪英格兰农业的地区专业化程度明显高于16世纪,非常聪明的方法(引文摘自: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p.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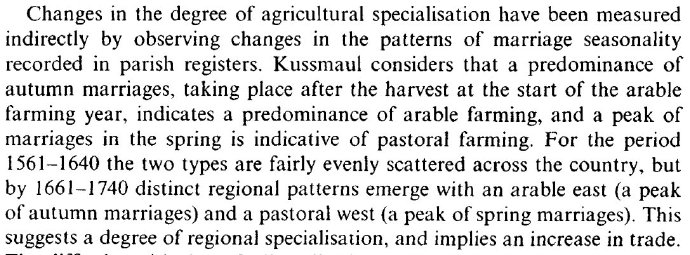
辉格
@ 2020-10-18 22:15
阅读(1,370)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0-10-18】
@whigzhou: 从1580年代到1710年代,耶稣会从里斯本向中国教区派送了几百位传教士,其中大约50%死在海上,他们的航程通常分为两段:里斯本-果阿,果阿-澳门,看起来每段的死亡率将近30%,考虑到新派出的传教士大多是三十多岁的健康壮年人,死于酗酒/打斗/事故的也极少,普通船员/乘客的死亡率只会更高。
@野人闲谈历史:托马斯•索维尔的《美国种族简史》中说,18和19世纪,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奴,路途中的死亡率估计是9%到16%
@whigzhou(more...)
8327
【2020-10-18】
@whigzhou: 从1580年代到1710年代,耶稣会从里斯本向中国教区派送了几百位传教士,其中大约50%死在海上,他们的航程通常分为两段:里斯本-果阿,果阿-澳门,看起来每段的死亡率将近30%,考虑到新派出的传教士大多是三十多岁的健康壮年人,死于酗酒/打斗/事故的也极少,普通船员/乘客的死亡率只会更高。
@野人闲谈历史:托马斯•索维尔的《美国种族简史》中说,18和19世纪,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奴,路途中的死亡率估计是9%到16%
@whigzhou: 不奇怪,西非到加勒比/南美的航线比里斯本-果阿要短且顺的多
@whigzhou: 葡萄牙航海探索的第一项重大发现就是:非洲西海岸的南半段不能贴着海岸走,必须先向西南,到靠近西风带时再折向东,所以西非-南美航线差不多相当于里斯本-果阿的第2个1/4
@winxpymaoo:谁给的勇气?金钱?
@whigzhou: 信仰,物质利益肯定是不可期的,他们留着欧洲的生活要好得多,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日本开始迫骇,众多教士被杀的消息传到欧洲之后,报名去日本者激增,许多耶稣会士都希望抓住难得的殉教机会
@tgyhr: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普通船员/乘客也应该是三十多岁的健康壮年人居多吧
@whigzhou: 有不少大男孩和青年,而对于多数流行病,三四十岁的壮年人免疫力是最强的
【2020-09-27】
读了Rob Iliffe的《牛顿新传》,篇幅很小的一本书,却完全颠覆了我对牛顿的印象,简单记录一下我的观感:
1)牛顿极度热衷于从纷乱世界中寻找出各种模式,这一点上,他非常勤奋,且兴趣广泛,也可以说目光十分敏锐,
2)可是有个毛病:他辨别和认定一种模式的阈值特别低,所以无论他将目光投向何处,总是能(自认为)发现一大堆模式,成堆成捆的,所以,假如你不限于公开出版物而检查其私人笔记和信件的话,会发现他头脑里充斥着一堆堆杂乱的想法,其中大部分质量很低,或者说非常草率随意,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这些东西也会让他显得(more...)
标签:人物 | 共同体 | 历史 | 思维 | 社会 | 科学 | 科学史
8287
【2020-09-27】
读了Rob Iliffe的《牛顿新传》,篇幅很小的一本书,却完全颠覆了我对牛顿的印象,简单记录一下我的观感:
1)牛顿极度热衷于从纷乱世界中寻找出各种模式,这一点上,他非常勤奋,且兴趣广泛,也可以说目光十分敏锐,
2)可是有个毛病:他辨别和认定一种模式的阈值特别低,所以无论他将目光投向何处,总是能(自认为)发现一大堆模式,成堆成捆的,所以,假如你不限于公开出版物而检查其私人笔记和信件的话,会发现他头脑里充斥着一堆堆杂乱的想法,其中大部分质量很低,或者说非常草率随意,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这些东西也会让他显得非常神棍,
3)依我看,他的这一思维特征和他的精神状况很有关系,可以说,他时常处于一种妄想症边缘的状态,所谓妄想就是模式识别阈值低,总是能从捕风捉影中发现各种预兆、计划、阴谋……支持这一猜测的线索是,他确实在1690年代经历过短期的精神崩溃,
4)而同时,毋庸多言,他当然是个罕见的天才,特别是数学天赋,
5)牛顿在有着上述毛病,却最终能够成就伟业,是因为:当时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而且共同体内已经有了一套规范,这套规范,以及共同体内的互动机制,最终将他引上了正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6)共同体对什么东西适合发表,并且值得被讨论和接纳,已经有了一些粗略的标准,这起了一个过滤器的作用,牛顿的那些乱糟糟的念头里只有极小一部分通过了这个滤网,进入讨论圈,为了发表,牛顿被迫把一些念头以可接受的清晰性和严格性表述出来,而被迫这么做时,他的数学天赋恰好派上了用场,
7)共同体内的互动机制,时不时会将牛顿的注意力强行拉到适当的轨道上来,也就是那些得到众多科学家关注,已经有了许多尝试和推进,已被界定和描述的比较清除,已经开发了许多实验手段,收集了大量原始材料的问题,
8)上一点最突出的例子是力学,力学原本在牛顿涉猎极广的研究中只是个小课题,而且他的路子完全走歪了,最初是胡克把他拉上了正轨,实际上万有引力定律的雏形就是胡克提出并透露给牛顿的,胡克和牛顿是老对头,关系很差,可是胡克自己数学不行,自知没能力从引力定律推导出开普勒定律,他知道牛顿数学厉害,所以压下积怨,希望牛顿能解决这问题,后来哈雷又拉了一把,需要求解的问题类似,只是用于彗星而非行星(和胡克相反,哈雷是牛顿的脑残粉),牛顿正是在解决这组别人找上门让他求解的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的体系,同时抛弃了他原本在歪路上形成的那些念头,
9)由此可见,科学共同体的存在,科学活动的组织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让我想起比牛顿早一百年的另一位天才,John Dee,同样才华横溢,牛顿要是早出生一百年,大概会成为另一个John Dee。
@whigzhou: 以数学论,牛顿在当时可谓傲视群雄,可是若以自然哲学或思辨能力论,我觉得伽利略远在牛顿之上

 订阅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