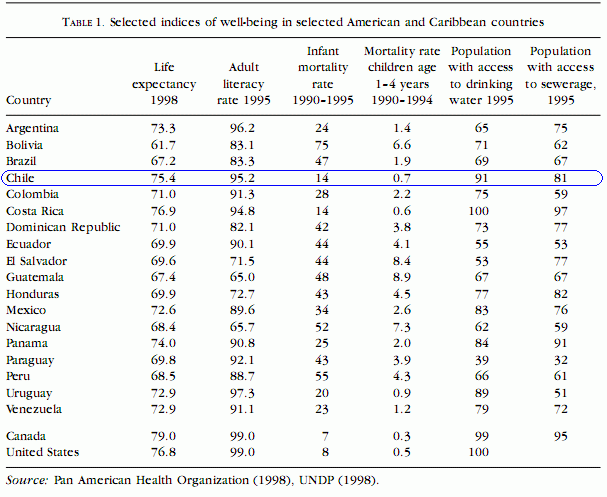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区分了刑讯逼供和刑求情报两种行为,北京棋迷提出了很多质疑,但我认为这些质疑所针对的,已经远远超出了我所限定的那种情形(我用定时炸弹的例子作出了这一限定,请注意,我未曾将之比附到任何其他案例上),至于具体的边界该如何划定,并非我文章要讨论的重点,这么做对我既无必要,也非能力所及,但既然棋迷同学在此问题上非常认真,我就再澄清一下。
首先要强调,我并不认为刑求情报就是合法的,我只是认为对这两种行为的合法性判定,应适用两种不同的法理,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它们被混淆了。
可能你会问,我只为刑求情报的合法性规定了一个抽象标准(犯罪行为是否已经结束,是否可能造成进一步伤害,刑求获得的情报是否能够避免继续这种伤害),那具体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或者是否可能存在这样的边界?如果无法划定边界,那岂不是跟黑狱私刑党卫军克格勃没差别了?
我的回答是:1)边界肯定是必须的;2)边界是可以找到的;3)但你要问我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4)给我具体的案例,我可以说出是在界内还是界外,但我的判断可能会与他人不同;5)不同的陪审团和不同的法官对边界位置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但并不妨碍司法的进行,正是在对一个个案件的判决之中,边界形成了。
曾有人问某大法官,到底什么样的图片算淫秽?他的回答是:我看了才知道。这个回答很适合这里的问题。
棋迷同学的每一段质疑,都把我给出的情形通过类比,推演到了十分不同的例子上,以此作归谬反驳,但法律是不能如此漫无边际的推演的,每条法理原则为自己规定的适用情形,都包含了主观判断,比如我为刑求情报规定的三条(是否已结束?是否可能?是否能够?),都包含主观判断,因而每一步推演必须接受中立旁观者的直觉检验,如果通不过检验,推演便告终止。
实际上,无限制推演的话,许多法理原则将会相互矛盾,比如民法上有条紧急避险原则,我为救落水儿童,砸破一户人家拿走救生用具,我就可以免于侵权责任,而落水者的监护人还要给人家补偿损失,如果推演不受限制,紧急避险原则就与财产保护和契约自由原则矛盾了。如果你再往远处推:我路过人家窗下听见孩子嘶哑哭喊,可不可以砸破窗户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啊?我看见孩子在井边玩耍能不能把他们临时绑架起来啊?甚至,我看见你在抽烟,认为这将危及你的生命,我能不能把你的烟抢走啊?
法律推理不是数学推理,不能因为命题在结构和逻辑形式上具有相似性,就以为可以进行数学上那种无限制的恒真变换。最后,让我再次引用霍姆斯的那段名言吧:
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The felt necessities of the time, the prevalent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ntuitions of public policy, avowed or unconscious, even the prejudices which judges share with their fellow men, have had a good deal more to do than the syllogism in determining the rules by which men should be governed. The law embodies the story of a nation's development through many centuries, and it cannot be dealt with as if it contained only the axioms and corollaries of a book of mathematics.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订阅
订阅